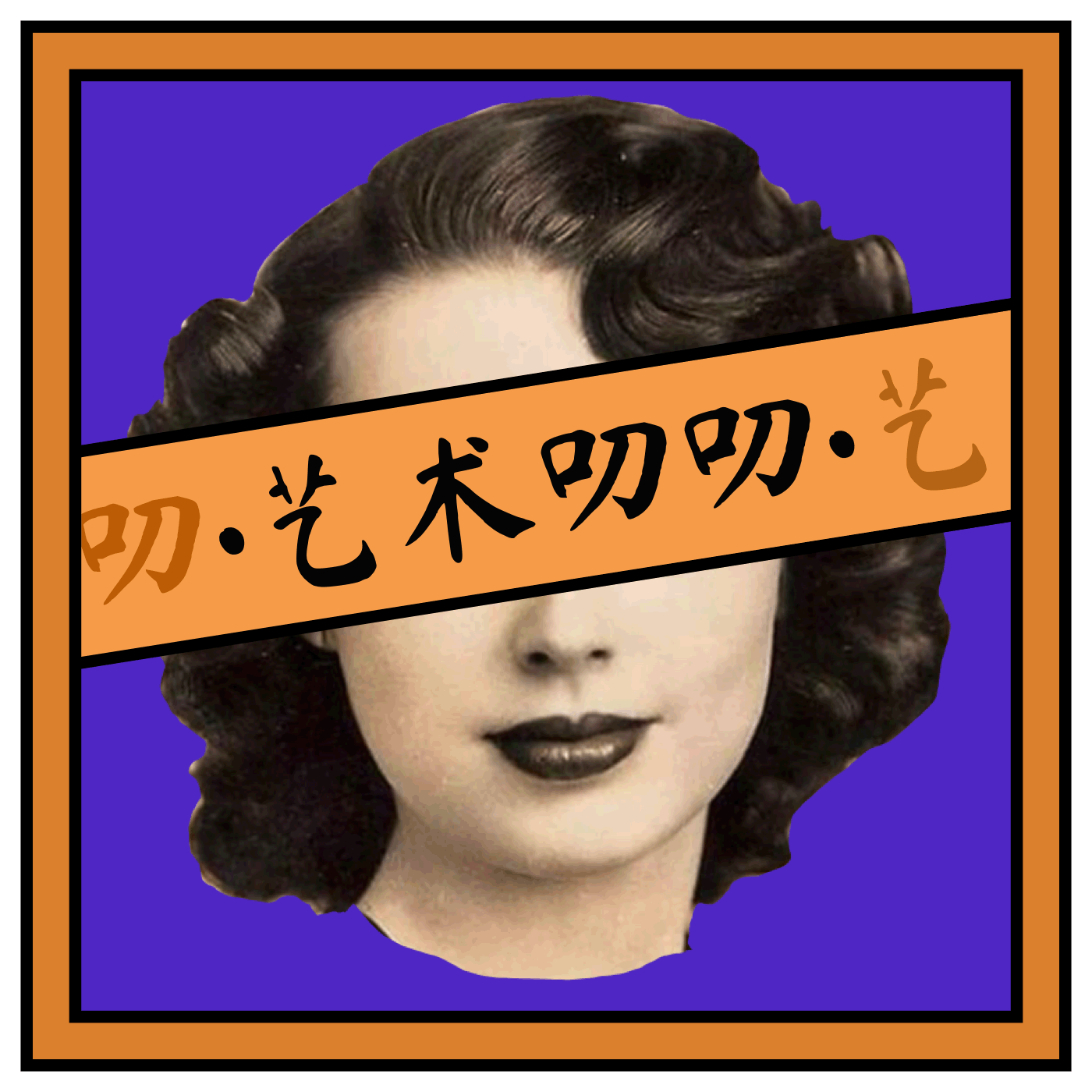
Deep Dive
- 杉本博司被誉为“宋朝摄影师”或“超越时间的摄影家”
- 其作品引发对时间、生命、死亡等存在主题的思考。
- 节目嘉宾对杉本博司作品进行多角度解读,包括其创作过程、作品呈现方式和艺术地位等。
Shownotes Transcript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艺术刀刀,我是 Money。大家好,我是兰意。那么大家都知道最近在北京的 UCCA 正在展出的就是山本博斯的展览《无尽的刹那》。刚好兰意其实原来在伦敦看过这个展览,她不太喜欢这个展览。
本来就一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来详细地聊一聊山本博斯那么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UCCA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张南昭老师我们先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UCCA 策展人张南昭然后
然后我也是这次展览无尽的刹那的资产人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有关这次展览和有关圣诞博斯先生的创作欢迎欢迎那么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就是目前正在牛津大学读东亚摄影的博士 Ellen Wang Yiwei
Hello,大家好,我是 Ellen,然后我这次还没有看过 UCCA 的展览,和蓝艺一样也是看了之前在伦敦黑卧 Gallery 的展览,然后也很期待今天了解到更多北京的展览。嗯,那我们先请张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在 UCCA 北京的展览吧。
没问题这次 UCC 在北京的展览也就是圣诞博斯先生的《无尽的刹那》这次展览是他在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这种机构性质的回顾展我们也是囊括了他从他的 70 年代也就是在创作生涯最早期开始一直到我们开展前夕 2023 年这跨越半个世纪的这些作品所以是他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是最大的一次回顾性质的展览
嗯那我们先采访一下艾伦吧嗯你应该不是第一次看他的作品了但是你第一次去到 Hayward Gallery 看到那个展览的时候你对他的作品印象是怎样的呢嗯
我这次对山本老师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评价是我在一个 interview 里面读到说他自己戏称自己为一个宋朝摄影师或者是在这边被称为一个摄影被霸凌前时间的摄影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让我感觉特别的合适因为包括它好多的关注的对象啊像实景模型或者像建筑都是一些在摄影术在 19 世纪早期发明之前就有的为了保留历史中这种世界文化而发明的技术吧就是这种对时间的思考然后
我觉得特别的评价对他很合适那兰艺呢我其实就是通过上一次在黑卧 Gallery 的展览才第一次看到山本老师的这作品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回顾展比较完整的去了解了一遍山本博斯的艺术创作脉络就是他不同的摄影系列其实对我来说完全是从一个什么都不了解的状态然后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展览我觉得就很好的梳理了
他的创作然后我之前就是在我们的年终盘点节目里面其实有简单提到过这个展览我记得我当时说的就是我觉得山本博斯他还是一个非常能够给观众带来启发的一个艺术家就是通过他的
创作方式通过他思考的一些话题我觉得就是给我自己也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因为山本博斯老师也是现在 76 岁了我开始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好奇的就是包括也没有在展览里面看到关于他早期的一些生活就他小时候的经历的一些描述所以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他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战后一个中产家庭的一个孩子就他爸爸那边有一个自己的小公司然后他爸是一个业余的诺语爱好者就一种传统艺能类似有点像相声但是也不完全战国司在本科的时候他去的是立教大学也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私立学大学然后他当时学的是经济经济和
有一点我觉得是可能过往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就是日本在 50 年代的这个安保斗争对于圣梦博斯的影响因为圣梦博斯的作品中很少会展现出这种政治性或者说它是一种很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但是战后的这一批尤其是就像圣梦博斯在某一个日本的采访里他提到自己的这个大学毕业证因为安保斗争它是一个 50 年代日本大学生
尤其是以东京大学为首的首都圈的这一群大学生包括一些人间活动人家对于政府和美国签署这个人民安保条约的抗争的这么一段学生运动吧我觉得就他在早期接触的佛教比如说这次他写这个《行经》的时候他提到色即是空空敌是色这句话实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思考但直到他晚 76 岁 70 多岁他才觉得自己很像一代了
他就这句话的真理说回到他的年轻的时代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想要去美国然后他去了那个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但是他自己经常在很多媒体上都提过他说他自己去艺术中心其实没学到什么他只是为了拿那个 Visa 为了签证对对对就为了那个签证然后他自己没觉得学校交给他了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去之前就不会拍照对我觉得就是山本博斯他是怎么走向摄影的这个历程也还挺有意思就是其实他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对艺术有着天然的兴趣的这么样的一个艺术家就他以前其实是比较喜欢木工和科学就这种比较理工科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火车模型然后就给
手办拍照的这种热爱然后才开始入门了摄影然后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就是加入摄影社团大学的时候大学本科的时候就是开始发现自己有一些设计海报上面的天分然后才就是转向了艺术其实我觉得他本科就是学经济学和西方哲学这一点还挺东亚家庭的一个期待吧然后其实我也挺好奇就是他和家里人啥关系就是
他家里人其实当时是支持了给他去美国求学提供了资金是吗他家是那个经营美容美发用品的是吧对其实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中产就是小生意大概是这样
当然我觉得家庭的支持是一部分然后但是另一部分我觉得是他自己个人的这个信念我觉得他年轻那时代的这些故事我觉得至少在我听起来总觉得他的那种非常一根筋的那种精神我觉得是致使他能有今天的成绩
因为他提到他自己毕业之后然后搬去纽约他还做过婚礼事业他自己还当时做了名片那就很失败他还尝试过做 fashion stop 他也觉得也不行他不太想被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它的厉害之处在于我们这次也展出了那张作品就是它那个标题是北极熊在透视画馆就 Diorama 那个系列下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大大学后几乎是同一时间的作品 74 年毕业那张照片应该是 76 年拍的在这别后两年他拍的那张照片立刻就被 MOMA 纳入管车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虽然这也有这种时代的红利因为当年的 MOMA 还是有这种 Portfolio Review 制度的就是伊斯兰可以向不同的 Department 提交自己的 Portfolio 如果这个 Department 的负担人觉得好就会联系你而且也是当时应该 MOMA 刚刚举办过当那个 Sakowski 设立的 New Japanese Photography 就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对于就是把日本的摄影带到来西方的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是 74 年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关注的更多是像那种战后纪实多一些所以可能就是跟山本若斯走的路风格还不太一样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时间点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不知道他当时可能会不会在纽约有一些跟这个相关的经历
我觉得他就如果你把他放到这个战后摄影的这一波日本摄影师里去看待的话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就是有点缺失的一种看待他的方法就因为像他自己无论是在他的剧专里还是采访里他经常提到的就如果说他会提到艺术家他会提到可能三四个人杜尚刚刚这儿单飞的就是我们可以大概从他的这种对自我的描述中看到他的这个谱系其实是跟战后摄影
日本摄影是完全不同的路线我想说刚才提到他的早期经历我还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想问问 Neil 的事就是关于他做古董收藏的这个经历因为之前 2015 年伦敦的那个巴比肯中心还展过一个就是关于做收藏家的艺术家然后也展过一些他对于那种
还有一些日本神道的艺术品的收藏就是我想要了解你有知不知道他早期是怎么开始或者是对这个古董收藏的兴趣和经历早期就是没钱他当时他说他申请了他能申请到所有的方便包括最重要的那个古董的那个摩擦楼室然后同时他有孩子有两个孩子所以这种生活的压力但有
其实也是挺大的他就觉得纽约是一个蓝海市场因为的确是没有什么像样的这种东亚艺术品商店所以他当时就应该是他孩子刚出生的多久 79 年然后他就回到日本然后开始寻宝开始想找
找点东西拿回里面买但是他自己其实他完全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这点我觉得也是我从他身上怎么说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种一手经验的重要性他从来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背景和经验他只能靠回到日本去各种各样的想想看摸听别人怎么说通过这些方式来学习
但是他很快的我觉得他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这种有关古董或者古物的价值判断体系一般我会说古物而不是古董因为我觉得在中文语形中古董就它有某种高价值的含义在里面就但是商人博斯他所收集收藏的很多东西就只不过是来自过去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艺术品那他当时这个生意好吗就他自己说还不错
他说他刚开买了没多久然后叶扣勇找他买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到他这儿买了很多东西就基本是纽约当时的衣服圈很多人都会来他这买东西然后开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然后他说基本是到他的自己的作品能够稍微卖慢了然后他这个店就挂了那他还蛮懂经营的对我觉得跟那个时代也有关系就因为当时当年可能真的没有这种类似的
竞品出现在这个市场上包括我去那个 Martha 的时候我去看了那个当代债的它的图书馆然后当代债图书馆里边有很多日本艺术品的书而且是那种日本进口日本艺术品的书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也从侧面印证我觉得它的就是在纽约当时的这种艺术文化权给当时的艺术家造成了一些影响
但你刚才说叶可勇找他买东西啥的我也挺好奇就是他在纽约的时候就是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其实他也是二十四五岁才到了纽约他怎么就是打开自己在艺术圈的这个社交圈的他好像有很多艺术家朋友在纽约是不是对他最近的这些动作里其实提到了一点他提到了那个谁何元温提到了那一代的很多
我是一身艺术家名单友人就是他的印象里比如何元湾是一个比较不和人来往的人所以他们也太差跟他很好然后他提到了那个蔡国强他说他当时搬去纽约的时候相当于先来跟他打个招呼然后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早期的一些互动我觉得当年我倒没有特别了解说他是怎么在
纽约首首但是我觉得他更是一个更 care 自己的创作的艺术家就包括他自己的早期的一些很多个展如果很早期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找他的资料的话会发现其实早期是在日本的画了
就在东京一个叫南化浪其实跟今天我觉得很多亚裔或者中国艺术家在纽约的境遇其实可能有那么一点像就你 base 在纽约但是可能你的 gallery 是在中国然后你的个展是在中国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比较的所有这种 minority 艺术家都要面对的一个
对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幸运的因为你想他在 74 年的时候搬到纽约然后 75 年开始做投射画馆和剧场这俩系列 76 年就被 MOMA 给收藏了我觉得这是开挂的时间线简直但是他收藏只收藏了一张一副然后给了他 600 刀虽然现在我觉得听起来很厉害但是他自己没觉得那是个多大的事对的
对但是我觉得 Mama 还是挺厉害的他们现在手里会有他那种很早期的 print 从学生时代毕业没多久然后当时的这个 print 对还是挺厉害的对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像运气很好我还看到说他被那个 Leo Castelli 给介绍到一个很厉害的那个画廊就是 Elena Sonnabend 对那个也是对他来说挺重要的一个画廊
你想对于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艺术家这个难道不是很好运吗是但是那一批艺术家我觉得都是有点这个运气我觉得运气当然是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我觉得他们的对于自己创作的那种坚定就是非常的坚定自己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比较稀有的而且也是能很有感染力的吧对有打动到这些人
就我觉得他们不是很在乎就是这么说如果我们去翻就是这个摄影史就甚至到今天美国的这个院校的摄影系统当中就是如果回到 70 年代他们看的东西可能是类似于 Robert Frank 或者 Lee Flander 或者 Walker Evans 就是那种类型的即时摄影带有着某种社会面向的这些即时摄影就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校告诉你的东西你当然需要消化当然需要理解但是你会
把它认作是某种样板或者是
或者某种模板尤其是艺术史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既定的事实然后你需要 work 相当于基于这个去做一些什么但是我的观察是很多艺术家他们会过度地关注于艺术史而不是相信自己的一个判断所以在圣摩斯他的早期第一个系列的作品《脱出画馆》他当时要做的一个事就是他想批判这种技术摄影他觉得摄影本身是一个骗局
所以我觉得这种勇气和这种对于自己相信和坚定事物的执着我觉得是很可贵的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三个系列然后分别展开详细谈一谈我们可以先从海境系列开始聊吧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挺平和的艺术家
其实大家都会去拍海但是他拍出来的海会给我一种很有禅意的感觉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他海景日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非常的接近于抽象有点让我想起来 Gursky 有一张就是他们卖的很贵的那一张
还有我觉得去那个黑窝展览给我最大的还有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作品去现场看然后跟在比如说在电脑屏幕上看感受就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他用的这些技巧吧或者他用的那个大画幅相机就是我觉得他的有一些比如照片上的包括他的大小
然后还有那个照片的 texture 和质感和细节是你在屏幕上看不到的我就觉得从他的这个最后表现出来的这些 prints 照片是可以感受到他后面的创作的这些投入的过程的
嗯,我是其实是在他那本书,就知道长出青苔的那本书里面,他应该提到摄影对他来说就是想要去呈现个人的记忆,文明的记忆,以及人类全体的记忆,然后他为什么对海有着独特的情感,是因为他非常确信他拥有的记忆就是海的记忆。
然后他原文是这样写的,他说晴空万里,锐利的水平线,从无限远的那一方拍打过来的海浪,当我看到这幅景象时,在我的同志之心中,有什么东西从久远的梦境当中苏醒过来?
所以我在想说海对于他来说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在他的人生当中不知道我们可以请张岚昭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 UCCA 展览海景系列它的一些内容的呈现海景系列这次因为他的这个系列我觉得看得比较多之后容易形成一种视觉疲劳说实话尤其是在你面对超过
也就是这个画面的下半部分
这个光是一点一点一点占据整个画面然后直到他们离开这个 section 最后一张作品是这个下半部的这个海是全都是白色的最亮的状态然后天空是黑色的然后对面那种是白天然后也是他们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顺序然后到观众离开这段区域的时候整个画面会变成一幅几乎是全白的一张画
就所以从进去的这个全黑到离开了全白我觉得通过这种作品的选择吧我觉得能更能给观众一些线索跟这个思考的内容对而不是被他的这种意义上的抽象性吓到其实我当时在看展览的时候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他其实拍的不是同一片海
就是他是到不同的海边去进行拍摄然后这个也拍了挺长时间好多年是不是对他到现在也会拍这是一个还在继续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系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在描述自己这个系列的时候也说到他站在海边思考的是我们看到现在社会的面貌和
几千年前看到的古人看到的面貌是不是一样的他想了很长时间其实就发现可能我们看到的海是同一片海所以说不断地在发展这个海境的
系列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布展观众会不会就是误以为这是同一片海因为他拍的并不是海岸的那个景象而是说而是海水和天之间的那个海天一线很整齐的那个海平面就是张海心里会有 captioncaption 的标题就是那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位置他的名字所以
如果是一个细心的观众他会知道这不是一片海但是我觉得这种对不同地域海的这种同一化处理我觉得也是这个作品很巧妙的一点就是它是同样的但它又不是同样的
我觉得这种非常对立的统一其实也是申梦博士他作品中或者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方方面面都会经常出现的一个逻辑吧包括这次展览的标题《无尽的刹那》其实也是两个含义相对的词语《无尽》和《刹那》
这个标题它其实不是从英文 time machine 翻译过来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新的标题因为就像博斯过去的这样的标题无论是在日语语境还是英语语境我发现他起标题喜欢是在这个语境的内部比如说 time machine 它是一个在英语里非常
然后观众一听就大概能知道这是在说什么比如相机作为一种时间机器或者说拍摄影作为某种时间机器它要 capture 固定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一个非常 straightforward 且符合英语语境的一个标题但是如果你把时间机器或时光机拍成中文然后我就跟上游说我说这听着特别像哆啦 A 那种电影他就抱歉了
然后我说那我总经想着他说他不想听讲讲多来一幕然后我说行就我当时也翻了翻他这个日语展览中的这个标题也是很难翻译包括他英语之前还有一个展览叫 B.C 就是那个就是 BC 就这也是一个你没法翻译的一个就英语里才能用的东西或者说你都叫 BC 就中英都一样但是反正也不行然后他的日语里的过往的展览比如说历史的历史就是
也不是不行但是不太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就是那是历史的历史包括它之前最近的一个展览叫本歌曲但这也是一个日本的文学当中的一个题材所以你也没法就是用这种东西所以其实在这个展览的筹备很早期我就觉得这个展览的中文标题
需要在这种东亚的文化内部去寻找一些相似的东西就它更像是在文化内部去寻找一个共同的连接点而不是进行某种翻译那你当时就是向山本老师提出这个标题的时候他啥反应然后我们这次展览的那个入口处可能你在网上都能看到这样的照片就是有一个用毛笔写的无尽的刹那的那个字就在入口的一个连接点
一个帘子上他当时就觉得这个标题特别好然后他自己就写了所以这个展览的标题是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怎么说思考的方式吧我觉得这个标题比黑卧盖尔那个更能让我 relate 到他的创作我觉得黑卧那个标题确实是提给西方观众的
对它是一个非常符合英语语境的一个标题那我们再谈谈剧院剧场系列吧因为这个剧场系列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震撼蛮大的一个系列因为它拍摄的设置的那个曝光的时间刚好是一部电影的时长所以说
它比如说曝光一个多小时首先我觉得它的相机设备很好很高质量就不会报废了拍完以后这完全不是相机的问题这是它个人技术厉害之处真的吗为什么怎么说因为大画幅相机只要它是大画幅相机它的几乎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大画幅相机的这个结构非常简单就是小拱成像它不像比如说 135 就是 35 毫米相机它有单反
有旁轴就精巧的结构但大复复相机是一个非常结实然后也是非常古老的相机就它不会出错就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的相机老了旧了就它可能会漏光那基本就是前面两块板跟这儿
像布袋的结构中间的区域就百分百在黑暗当中有光扑过来它其实不太是一个靠机器本身大核相机本身它就是一个成像最清晰的一种相机了它的志愿系列对我来言它的技术上的高水准
我觉得是很难很难去复制比如说看到摄影作品就是我们大家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比如森山大道式拍摄然后就一堆摄影然后就拍得跟森山大道基本一模一样或者说什么荒木精美式就用彩色的非常鲜艳的或者什么川内轮子就几乎已经变成了某种滤镜就你一拍放一个滤镜基本跟那个摄影师本人拍的差不太多但上伯斯的这个居愿系列我觉得就是能够成功复制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为啥呢就是如果你们拍的照片你们知道的如果一个地方 contrast 就是它的对比度过高白的地方巨白黑的地方巨黑就它的这个 balance 平衡是很难去控制的它的这个照片如果拍不好很容易变成中间那块白会变得非常的显眼然后吃掉周围一切的暗部细节就是它的这种技术上的控制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贯穿它整个创作的一个
特点吧就是实验性就他是一个自己会通知通知做实验的就这个系列也是包括他有一次提到就他几乎是刚到纽约的时候就开始为这个系列做准备了然后他会去那个 San Marcos Place 在 East Village 那边的一些他说 B 级片电影院就很便宜然后他就会进去
然后午夜场他就会坐在最后一台加个相机开始试就跟他的那个放电厂就是闪电那个系列很像那个系列他也是试了五年然后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图像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跟今天很多的当代艺术家喜欢这种跨界合作是不太一样的就今天很多当代艺术家喜欢跟一个 scientistcollaborate 跟一个
某个领域的这种专家一起合作做一个什么上伯斯完全是他喜欢靠自己他喜欢自己一点点摸索比如说他的这个我相信今天可以有一些大数据能够
能够算出来你要这么长的曝光因为每一种胶片它的感光特性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持的我相信今天如果要用某些这种 tech people 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就这个电影然后你在这个关键条件下曝光曝多长然后你的这个快门各种设置是多少我相信这是可以算出来的但是它宁愿花五年几年的时间自己一点一点找到这个最 perfect 的这个顺序
然后做这个作品对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画面上虽然是白色的但其实已经放完了一部电影就我记得他在描述这个系列的时候他就说就是相机虽然能够记录但是没有记忆就是相机看完了一个电影它留下来的是一个白色的屏幕但是人
看完那部电影就是可以记下来就是电影的一个内容那我挺好奇就是 Alan 你觉得巨岸的这个系列你有什么感受我觉得其实这个系列也是我最喜欢的山顿波斯的作品的一个系列然后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非常多的摄影师都探究过就是摄影跟时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永恒的话题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它既然它所...
捕捉到的其实是摄影作为静态的一种单张和 movie image 和 cinema 就是和电影之间的关系然后被这个系列给捕捉到就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一秒有多少多少张的 singular 就一个 image 嘛然后但是我们觉得它在动其实只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但其实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些连续的
still image 的一个假象然后他我记得他也提到过就是他这个作品其实是把那个电影相当于变成静止然后 freeze 掉了然后就把他这些所有的这个一部电影时间中的这个时间然后给定格到了这个一张静止的图像上
我觉得是非常就是可以 moving image 和 still image 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对 Ellen 提到这个 moving image 的这一点其实我们在展览现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我们的每一张这个剧场系列中间那个白色的部分就它的这个相当于它电影画面的白色的部分我们都有一盏灯直接打在这个方形的这个区域中
这个灯这个光线本身的这个范围也是完全跟那个方形的屏幕吻合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灯就它设定了一个大概几毫米的上下抖动的这个功能它是一个肉眼非常就是你要仔细地观察你会发现这个屏幕是有抖动的就它其实非常像早期电影院也就是像门博斯拍摄的这些电影院放电影的那种胶片
如果你们看过这种胶片放映它最开始头上那几秒因为是透明的胶片光线穿过它它会有一种抖动的这种视觉感很多观众朋友他们在小红书各种地方他们都发现了这个事情他们都在讨论这个我觉得对观众的观赏能力非常强他们也能够通过这一种光线的抖动能够迅速地怎么说联系到刚刚 Alan 提到的这种静止的画面跟这种滚动的画面之间的有意思的对照跟反差
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想问张老师,就是在这个作品中,张本老师他对这个电影的选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支出,因为我看介绍他有一张是在美国,就是印第安纳拍的,他上面有写他放那个作品是,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我想说是他每次放的作品电影都会不一样吗还是说会根据这个他地点不一样而选择的电影也不一样他早期的那些 70 年代的那些作品他的这个电影放映选择不是他自己可以选的
基本是对方放什么他会拍什么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形成一个经验反正他特别爱开玩笑所以就是他说的话我觉得不能特别当真但是他经常开玩笑说这个迪士尼电影是最好拍的然后因为迪士尼电影都特别 happy 然后他们的画面都很亮这样提供的光线很足然后他说 David Lynch 那些 B 级片导演的电影最难拍因为都黑乎乎的然后拍完就什么也看不见他大概说了些这个我
我觉得他比如说放那个 Snow White 那个白雪公主结合他自己的这个画因为他的目的目标是要呈现这个图像我觉得某种程度他放的这个电影有一些现实的考量就比如说他测试了这个电影他熟悉了这个曝光之后他可能某一部电影比如说这个白雪公主他会可能播放几遍就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他的这个技术上的要求真的是非常高
我觉得他单纯的从技术上考量的话每换一个环境再换一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变量太多会导致他最后这个拍摄变得更加艰难就纯粹从技术上去分析的话对其实我看到就是剧院和海景这两个系列我真的是从他的这种非常细节控的工作方式上面就是给我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就是其实他本来
本来不必要给自己找这么多事,但其实他就是为了达到他想追求的那个比较完美的效果,所以说就是做了无数遍的测试,包括就是肖像系列以及就是那个花馆的系列,其实他要调光也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你觉得因为我看到山本博斯他是怎么又开始就是关注佛教关注日本文化他这个路径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搬到美国以后先在那个洛杉矶上学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那个时间点也是一个很妙的一个时间点就是 1970 年代左右因为那个时代因为前段时间读那个乔布斯传然后乔布斯就是那个时间洛杉矶硅谷的这些西匹士他们就对印度对于就是灵修对于禅宗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乔布斯也是在 19 应该是 74 年的时候他去印度进行了一场领袖之旅所以我觉得山本博斯当时就是到了西海岸以后其实有被那个震撼到因为我想他当时对于西方的想象就是可能他之前在日本学到的一些关于西方的
然后来到以后发现原来这里的人都对东方感兴趣那他再重新回溯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对于佛教对于日本文化的了解不如他想象的那么深厚所以再重新就是进行很多的研究这个对于你之前就是研究佛教这个路径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对我之前其实有一篇文章
论文其实有一点点是关于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佛教的西传大概 50 年代起有几位日本僧人吧比如说以林木大卓为首的这些学者或者
僧侣然后他们开始翻译佛经开始像把佛教系统的介绍到西方影响到了一整代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就这个知识分子是广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视觉艺术家是其中当中一部分然后包括其实像 Guggenheim 他们 09 年左右我又记不清具体哪年了然后他们做过一个叫 The Third Mind
的一个群展那个展览其实某种程度上关注了那一代从 50 年代起的美国艺术家们对于佛教禅宗为主的这些佛教思想的关注和他们做出的回应所以某种意义上山本博斯其实也是在这个叙事当中的
包括甚至很多中国艺术家其实也是这样像徐滨他的一本画册当中有一张图片就是他最早接触到的一本有关禅宗的书就是林福大佐写的《禅与生活》我印象中那个是 title 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从二战后的这一批日本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就首先是学术界然后到思想界然后艺术界然后这些东西又随着当代艺术的全球化又反过来影响到来自亚洲的这些艺术家就换句话说像圣本伯斯包括徐滨他们认识佛教不是通过自己而是通过他人
所以其实他对于佛教的这种研究有什么具体的表现之前就是你们在做媒体导览的时候山本老师还用日语读的那个班罗波罗蜜心经我觉得那个还蛮震撼的听到他现场
嗯,对,没错,对,因为日语的发音其实听起来和寺院的发声方式会更接近,就是新代汉语中它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发音,班若波罗密新经,但是如果是日语的话,因为日语的语音它是有一种连贯性的,
它是可以连起来成一句的所以它更有那种怎么说呢寺院当中的那种宗教仪式性对像山本先生他我觉得他跟佛教的关系或者说他对佛教的影响佛教对他影响我觉得一大部分程度其实是得益于日本他现在的这些文化遗产的这些保存
比如说八世纪的佛像八世纪的这些木造建筑他们都还能看得到或者说被广泛地研究并且有各式各样的资料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他汲取这些来自佛教的营养的一个最直接最容易的方式吧
然后还想问一下 Neil 就是你在和山半老师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分享就他本人的那个工作状态是和他创作过程中的那个状态准备展览的状态是一样吗是我觉得他可能他今年 76 岁了我觉得他在北京待了一周多然后他每天都和我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6 点每天
每天都在那个展览现场对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是我因为我以前也合作过差不多年纪或者差不多级别的艺术家可能他们到这个年纪我比较习惯了可能他们会把很多事情交给他们的助手去做可能由于年纪或者由于这种展览经验就他们可能会比如说最后来看一眼就结束了但是他是从第一天他到北京到走之前一天他每天都在展览现场
亲力亲为的也是因为我看到他的那个建筑事务所做的展览空间因为我们上期就是正好讲到 Wolfgang 就是说他之前给那个 Tate 或者是他自己做任何展览的时候其实他都会做一个建筑模型然后在里面
做自己的这个展览就每个作品是怎么放在那个位置就还蛮细节的因为我和 Money 就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都还阅读了一下山门博斯的写作的作品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
相似的感受就都觉得他写的真的很好就是他甚至比他看他的作品更对我们有精神上面的一些冲击然后我觉得就是把他整个的一个创作
思路啊他做每一个系列是怎么缘起的都讲得特别清楚所以我觉得山本博斯是不是能够到今天在艺术界的这个地位也是和他非常会解释自己的作品相关我觉得肯定是吧我觉得这种成功艺术家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构建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宇宙在他们的各自的宇宙当中就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有一个
内在的因果和这种表面的连接会写会说当然是一个我觉得是艺术家来说很重要的优势吧当然并不是说会写会说就代表你的作品做好只能说是加分向感
那就是作为策展人,因为你也要比如说写一些展签啊,然后写签言啊,有很多文字的这些工作,那你多大程度上就是参考了他对于自己作品的这种解读,还是说策展人往往也会就是引入一些其他的视角?因为这次的展览 UCCA 是没有出画册的,
所以我们唯一的一些写作都是集中在作品的介绍然后作为策展人我需要写展览前沿前沿包括作品介绍的这个体材包括它的程度跟它的这个 purpose 它的需求其实不太用去参考艺术家的个人的这个 writing 因为它的 writing 是一个很具体一个非常根据
根植于他的创作内部的东西但是这种前沿我觉得需要提供的是一个宏观的东西所以在前沿里我觉得我可能就去更多的是去重新做一个他的历史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定位吧就是指出他
并不是在这个战后日本摄影师的体系当中同时他也不是一个那么在欧美艺术体系当中的一个这种双重属性就是可能认识山本博斯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观众尤其是在比如说书店山本博斯森山大道荒木精子这三个人基本上经常同时出现也挺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三个人永远都是同时出现的
包括他的名字可能会对很多观众会有一些误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日本的摄影师但是他又是继承的比如说他作为一个摄影师他经常提到的人是杜尚这个是个非常稀有的事情除了山本博斯我很少会听哪个摄影作为媒介的艺术家会天天提杜尚那杜尚对他的影响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当然是杜尚的这种现成品
的这些概念但是我觉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现成品就是将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的物品转换为艺术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理解我觉得圣本博斯更在意的是这种价值的转换因为圣本博斯从在度上那他认识到了这个有关现成品的概念他同样在古董古物当中也可以找到
比如说一个来自唐朝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碗它某种意义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
圣博斯发现的这种价值的转换他既是当代又是古代就这一点他觉得杜尚某种意义上帮他重新认识古代跟现在的关系所以我有点有一个问题想问艾伦就是策展人也有讲到他在写展览前年的时候会考虑如何把这个艺术家放在整个艺术史里面进行一个
看待和定调吧那你研究了很多的东亚摄影艺术家你觉得山本博斯他现在在整个东亚摄影史或者是整个艺术界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和位置上
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时间点到了美国我觉得单看过去可能 50 到 100 年摄影在日本发展的轨迹和在西方发展的轨迹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可能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摄影的机构化或者就是被美术馆
或者画廊收藏体系的建立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在美国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就在 1930 年代左右就有纽约的 MOMA 摄影部门最早的成立而在日本这个大概是 80 年代的时候而且它第一个就是专门针对于摄影收藏的一个美术馆是在 1991 年就东京的那个
Metropolitan Photography Museum 才建立的在山姆博斯他 70 年代到纽约的时候当时在美国这个系体系就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他会不会我想象被当时的那边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工作的方式来影响而且他做的作品你可以看都是比较系列化
然后而且是被一些比较概念为引导的就相比较其他的摄影师比如说森山啊或者中平卓马他们可能是更多是一种街拍啊或者是碎片化的就没有说一个不一定是特别明显的按照系列来工作这个方式就我觉得他的工作方式比较接近于一个当代艺术家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放到说日本摄影史的话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不能完全 fit in 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之前听那个熊小莫的一个节目他就是当时去年的时候来伦敦也去黑卧 gallery 看了这个展览然后他大肆批判了这个展览他说那个策展是一个很懒惰的策展
然后我听到这个我蛮惊讶的因为我没有觉得他很懒惰他的意思呢是说他很期待在里面看到一些关于艺术家创作过程的比如说文献啊档案啊一些幕后的照片这些但是那个展览中就只呈现了他作品本身以及他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展前其实我从这展前里面学到蛮多对可能我们这个知识基础不一样吧所以
这次 UCCA 的展览里面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做一些这方面的调整其实一般是这种离我们远去很久的艺术家会有这些文献的部分因为需要让大家回到那个时代他已经不是一个现代的人所以他的必须要靠这些文献去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个展览的一个上下文
其次还有一点就是艺术家有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这样去呈现自己的作品包括像沈本博斯他自己也说他说回顾展听起来是一个他死了之后要干的事他自己也不太想做回顾展不太吉利
我觉得不同艺术家对于回顾展这个事有不同的定位吧有的艺术家就很喜欢回顾展他们觉得自己能从做一个回顾展当中重新认识自己的作品但有的艺术家就非常不喜欢回顾展他们喜欢新的展览比如说像博斯喜欢北京的这个展览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他心里的尝试在空间上在作品呈现上在对于跟这个佛教的关系上我觉得不同的这种展览有不同的类型吧
我觉得我只能说就是文献的部分像 UCC 的话比如说我们过去的马蒂斯的展览会有很多的文献的部分比如说这种现代主义包括比加索这种艺术家会有很多文献的部分但作为一个在世艺术家我们印象中不太会有这种特别
关于他生平这些的介绍我觉得还有一点让我感觉因为是可能很多就更需要那个文献啊这些来 contextualize 就给他一个背景但是我觉得山本老师的很多作品都是觉得让人觉得就是脱离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让你不知道其实不太重要他是在哪里或者什么年代
所以也不需要这些就包括有的观众会说他说这个展览看完让他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挺好的因为都是照片但他又不知道这照片是什么时候因为一般你看到一个照片尤其是有这种建筑文可能会通过这个建筑人物着装可以大概判断这个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但看善博斯的照片就有一种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时间的感觉包括我们展厅整体的这种整体感又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展厅里有很多他的一个生平这些文献的介绍我觉得会对就像 Alan 说的我觉得会破坏这个展厅的整体感觉嗯
我想就是熊小莫之前提到的应该是他觉得就是山本博斯的创作过程就是还挺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他非常注重细节,然后会环长时间学习的东西,就比如说如果有什么第三视角的这种东西,他会觉得很期待看到这些吧,不过 anyway 我觉得这是一个,
评论吧因为他也做摄影什么的对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开展后有听到什么有趣的观众的反馈吗有两个吧说一个好的一个差的先说差的展厅太挤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山派老师低估了 UCC 的这个人流我觉得多的时候是有点挤然后好的 comment 是我开幕的第二天在展厅里遇到了三位比较年长的女生
女性观众大概在感觉在 60 岁上下吧他们这个年龄群体其实对于 CC 来说是非常稀少因为在中国大陆去美术馆的这种主流群体其实是年轻的女性然后或者情侣是最多的这三位观众他们当时在申本博斯的那个《心经》的作品前面他们就在非常热烈地讨论他们讨论完之后我就去问其中的一位观众我说您觉得他写的好不好
然后那个阿姨就连忙她就摆手她说她也不懂她只是听说这个展览就想来看看首先她觉得她不觉得这是一个书法作品然后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书法是用墨汁毛笔沾着墨汁在宣纸上写但是山本博斯是用毛笔沾着显影液在相纸上写
然后这个阿姨虽然她声称自己没有受过艺术史训练但她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媒介的差异性宣纸是吸水的但是相纸是排水的相纸的表面很像玻璃所以它的媒介特性完全不同所以它的确不是书法作品就那个阿姨就用这么几句话我觉得马上抓住了这个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并且阿姨肯定非常仔细地读了我们的墙上文字才知道这个善博斯是怎么做的
然后那个阿姨又说她说她觉得因为山本博斯这次的这个《心经》的作品是用毛笔沾着显影液在相纸上写字然后曝光所以曝光的地方是黑的它的字是白的
然后因为显影液跟相纸的这个接触方式在曝光它不会像宣纸那样是非常实的就虽然它用显影液在相纸上写了字但它开灯如果开得过快光快过了这个显影液跟相纸表面发生化学反应的时间所以它的有一部分的这个字是还是会有一点点黑有点点白
他觉得非常恰到好处
然后这个阿姨就让我作为自然人非常非常非常的欣慰她真的有用她的眼睛来去寻找她想寻找的答案太棒了有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可以从观众身上
身上学到很多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就聊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张南昭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策展幕后的很多的小故事以及细节我觉得确实是对这个展览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带着这期节目一起去看这个展览
山本博斯无尽的刹那然后也很感谢 Alan 来今天和我们一起聊聊关于摄影的这个主题然后也期待之后继续和 Alan 一起聊天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的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艺术刀刀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