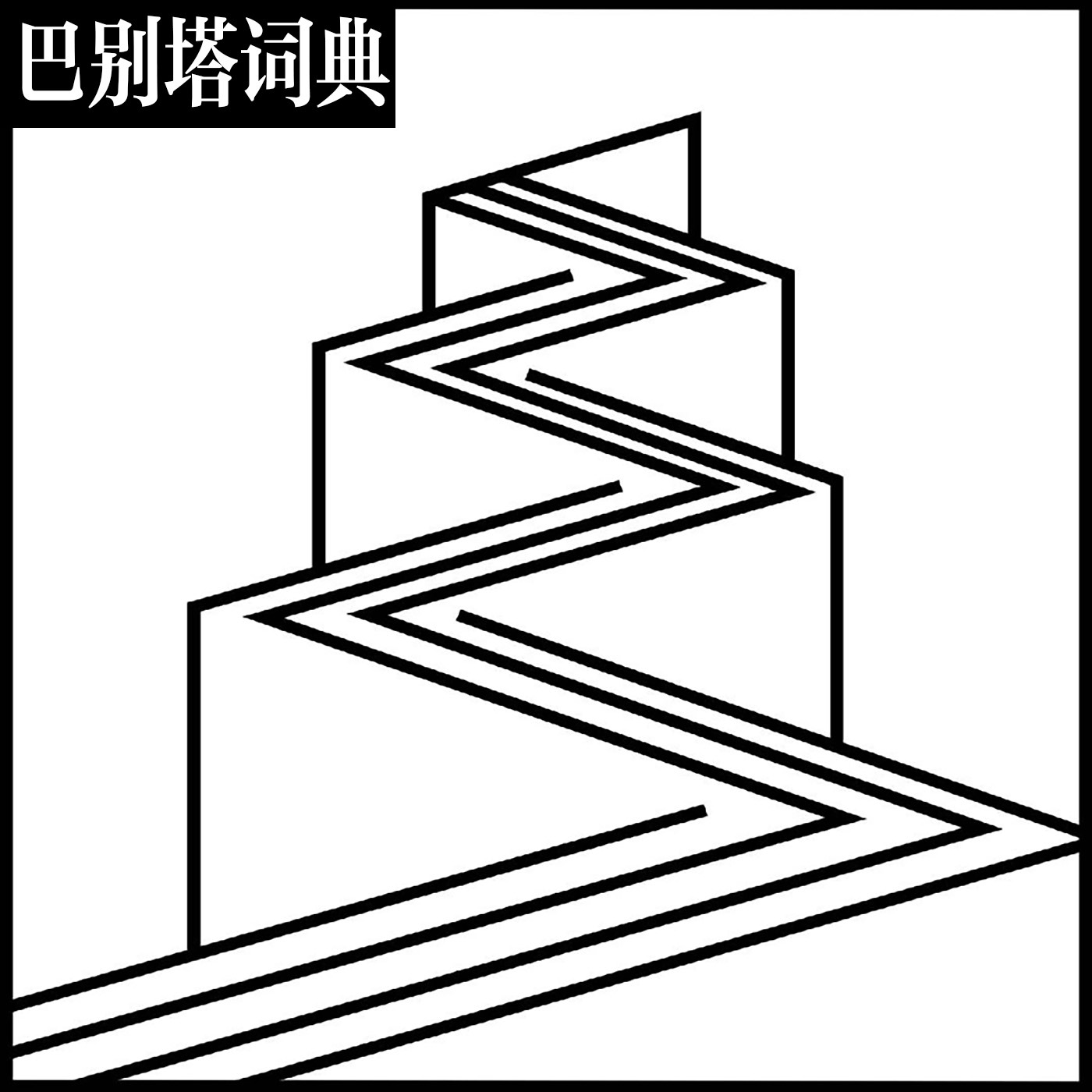Deep Dive
- 国学热在2000年后再次兴起,与百家讲坛等媒体传播有关。
- 国学热跨越年龄段,影响广泛。
- 当代社会中,即使不使用“国学”一词,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中也体现出国学的意味。
- 汉服运动是国学影响的体现。
Shownotes Transcript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辈塔词联 我是主持人姚天怡哈喽 我是橙子哈喽 我是朱熹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袁一丹老师然后欢迎他来参加我们节目今天我们谈的一本书叫做《国学臣服》然后袁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谢谢天忆的邀请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三位一起来聊一下就是最近新出的一本书叫做《国学城府》对对对,其实这是一套书中的一本这个一套书的名字叫做《慢说文化从书续编》是由钱丽群、黄子平
陈平原老师策划推出的这个原来的一个系列慢说文化重书编出了 30 年之后这回陈平原教授写手另外 12 位学者推出了这个续编然后袁老师也是其中之一专门负责这本关于国学的作品所以呢这次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更多的还是就这一个话题因为最早这个推出方嗯
领读文化编辑老师找到我的时候就想询问我们嘛作为我们播客哪一本书可能更适合我们这个调性其实袁老师刚才在那个录制之前呀也向我们表达了一个就是疑问就是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国学臣服这本书包括这个主题感兴趣然后我这里也想就是简单的解答一下因为这个选书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但我也投了这一票赞成对对对大家的投赞成对我们三个人吧拿到两票就可以决定了
是其实选这本书主要是因为从我个人来讲有一点的这个个人经历的元素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长大到可能 08 09 年那一段时间在学校的时候你很难逃开就是当时百家讲坛的这个电视节目的影响
然后也是从那个角度我了解了所谓的这种国学热就是当时那个国学热的现象你像当时的一中天或者是宇丹他们讲这些不同的历史或者文学经典等等就这些内容我觉得是非常弥漫于当时的那个互联网或者人们生活的环境的那个渗透率是非常高的
只不过可能现在十多年过后大家已经有些淡忘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确实就像包括这个书里面其实也有地方点到了就是在那个时候的那样一个井喷式的媒体产出在大家的无论是网络环境里面还是生活环境里面形成这样一个个的小圈子或者一个个的小团体大家重新对一些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一些什么文化习俗这些东西围绕他们建立成了固定的兴趣团体或者爱好团体
然后这个还是跨年龄段跨度还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袁老师刚才还问我们觉得可能国学这个话题离当今的包括离我们巴贝塔词典这个主题可能稍微远一点但我觉得咱们可能还是因为听众或者包括我们自己平常爱好的限制导致我们并没有去注意到一些其他角落或者我们容易去忽视那些地方但其实我觉得那些地方那些圈子里面的讨论等等他们的活动还是非常活跃的
不就我大学同学我的一个感觉是只是说可能在 2023 年的当下可能有些人不使用国学这么一个词语但是他们做的事他们所认同的观念或者他们所践行的一些具体的行为是有很强的国学的意味的嘛
对比如说如果我们回到 80 年代那个时候没有汉服这个具体的词语但是很明显新世纪以后的所谓汉服运动你把它放在一个国学这个问题的视角下你是能解释得通它的逻辑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明和实的问题对
我也想先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在《血编》里面会有《国学臣服》这一本书最开始陈明远老师找我们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还特别的风雅我们去了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大家可能知道来金雨轩在民国的这个文坛里面它是一个雅极的场所当时刚刚恢复营业的重新开放的来金雨轩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就聊选题
当然陈老师他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划他提出了一些选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 12 本呢大部分是在陈老师的一个规划当中但是恰恰是国学臣服这一本一开始并不是陈老师考虑的范围陈老师一开始是希望我看到他的小本子上给我写了一个选题叫做琴棋书画因为琴棋书画是大雅嘛嗯
也是 20 世代以来特别是文人社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选题当时我看了这套书以后呢就是这个书的这个规划以后心里面稍稍会觉得自己觉得有一点点欠缺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小书大家看到它的开本并不
是一个小书但是它不是市面上一般意义上的风化学的软的读物对吧它虽然是一个散文的选本但这个散文的选本它不是情感像的或者不是那种轻飘飘的一种快餐性的大家是希望说这个选本里面呢它是软的但是软的里面应该有比较硬的一些东西被包裹在里面
所謂硬的東西就是希望他能夠了解大家通過這些文章不同角度的文章能夠了解到我們是從改革開放以來這 40 年的一些風氣的風向的轉變剛才天一談到一個詞叫做瀰漫或者說瀰散其實在
我们的每一个社会的节点刚才谈到 08 年前后或者什么样的在每一个社会节点这个社会里面有些空气这个空气是文化的空气思想的空气那这些空气它可能会落到这些文章里面所以我当时一开始我并没有马上直接的想到国学的这个话题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说我自己希望做叫做学人心态的这样的一个选题
学人心态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他在经历大概从特别是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再到 2000 年以后知识分子他是比较敏感的一群人那他们在这个社会的位置的变化总体而言是去边缘化的
那他們對於這個社會風潮的一些反應所以一開始我大概想的是學員心態的這樣一個話題但這個話題有點過於的寬泛了所以再往這個方向再往知識分子的心態史再往這個方向再梳理這些話題的過程當中發現國學是一個比較能夠聚焦的一個話題
所以最后我跟老师说我要报一个选题叫国学臣服老师当然同意了但是他提出说这个话题有一点点沉重跟我们整套书希望在轻和重小与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话那无以国学臣服这一本它在整个书的选目里面是偏于重或者说大的一个选题
那怎么来调剂它怎么通过选文把这样的一个很沉重的或者是过于庞大的偏于思想史的这样一个议题让它变得可读可感把它跟一些社会的热点结合在一起是当时选的时候的一个考虑所以从情趣书画到国学神符这个
这转变还是挺大的但是希望就是我是希望有这样一本在整个虚编里面看起来稍稍有点特别的说呢让这套书它的整个的它有一个更加下沉的或者有一个相对能够重的一个层面来折射这 40 年的这个风气的转变当然我想我不知道三位是不是应该是 90 后还是应该是 90 后我们有一个 80 后
八年后 那我也是八年后所以当然我们在刚才谈到的大学时代或多多少少都经历了第二轮的国学热特别刚才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通过百家讲坛通过像于丹像一周天这样的人极大的放大了国学
他的影响远不止于这个学院体制他放大了对社会层面的这个影响甚至会改变大家对于学者的一个看法比如说我回老家告诉大家告诉他哎你是做学什么的呀我说我学学中文的啊他说学中文的那你如果
你能像余丹那样上百家大讲台他们对某一个专业的想象就被余丹或者是被有一些比如说唐诗颂词的这样的一些通过中央的这些媒体电视媒体就被他凝固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我很难跟他解释说我做的这个学术研究跟一种
他们做的这个传播的普及的工作的区别但可以想象就是说国学的通过跟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它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辐射性的这个效应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它虽然是一个偏于学术思想的话题但是确实又跟当下的这个媒体的环境跟我们的这个社会氛围有很多的关系其实老师刚才讲到有一个点我想到的
因为您说最早的规划是琴棋书画嘛但事实上在我的观察当中琴棋书画在很多人那儿就跟国学这个概念是高度互相绑定的他可能会把那种你擅长于做这些事就会视为你是一个风雅之士的象征甚至说他还和那个时候的一些教育系统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觉得我家有个小孩我训练他去学一些这样的东西对他以后比如说去呃
上学的时候作为一个什么特长啊或者说他以后出去的时候对他什么个人素质啊包括说他去社交的能力有一个帮助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一个挺明显的趋势的对刚才您看到这一点就是他其实国学他不仅是一个知识他变成了一套想象这个想象特别重要大家
那怎么来想象这个传统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这当然包含了经典的这个重新的被阅读 吟诵这是一方面还有包括诗词歌赋的这样的一方面还有就是你刚才谈到特别重要的一面就是跟这个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这个风雅
或者是变成附庸风雅现在我注意到学古琴的人特别的多对琴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符号当然还有一个刚才谈到的汉符的问题其实汉符是一个特别有症候性的问题
我是前两年是在杭州待了半年发现杭州一到春天花开的时候在西湖边上或者是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穿着汉服而且甚至我觉得汉服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形成一些小的群落对吧汉服里面可能还有不同的派别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未必是不基于刚才主席谈到就是不基于民啊
我们如果说不距离于国学这个名的话那事实上国学的影响已经慢慢的融化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层次当中去了在这里我也想就是补充一下关于两个词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是散文二就是关于这个话题作为一种这种知识分子的学术焦点这个问题因为最早也是就是编辑老师把这一套书拿给我的时候说这一套书都是散文集所以我的一开始的一个预期就是说这个书里面的文章可能
会比较泛泛的把这个话题给谈一谈只不过是因为就刚才谈到就是因为国学在我的这个童年可能有一个留下了一个印记所以我选择了它但是我这个书差不多就是一翻开我就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哇我选的真对啊就自己表演就因为它里面这种文章的这个结构形式让我觉得非常少见的特别是在这个中文的文化圈啊就是你非常集中的
把这种就同一话题的不同方面的他甚至有一定这个辩论性质的这样一个文章集把它这样编排出来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怎么说你就针对这个问题这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个讨论方式至少这种这种思辨的这种对话的方式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至少我个人是比较少看到因为大家可能现在都是
看的比较快的东西包括你像那种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上面发的那种长文章他也没有达到说当时那种纸媒上面发表这种社论或者这种个人观点这样一个格式下来的那种氛围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有价值了
然后再就是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焦点这个点其实我觉得虽然大家有些文章在里面是看似是互相在驳斥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大家未必谈的是一个东西不过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你很容易就看出来各个人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看似在对立的地方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说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在某些事情上面不一定有想象的那么对立等等然后在国学就是您说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充满想象的一个词汇就是不同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就是他从很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
他在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里面表达的意思然后在平民中表达的意思引起的联想都是截然不同的包括刚才提到那些情绪书画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在我的联想里面就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东西跟真正学的层面在我的最初的想象里面还是离得比较远的因为我就像刚才说的包括我刚才也可能就是潜意识的在提到的就是说
我会把这种什么经典的文学具体的文本一些东西史书这些东西可能当成一种国学的这个最主要的部分然后确实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等同的就是把这种历史的学习或者这种文学的一种学习把它等同于当时的那种国学但其实也不完全是嘛刚才主席也提到了所以我觉得至少在这些层面这本书可以
提个醒吧就是第一就是确实你还是能够在一些地方就是对于可能我们有一些比较对这种文化圈心灰意冷的听众就其实在有些层面你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比较有价值的思辨的就算你对这个话题可能一看是国学什么东西就是你对这个话题也许没那么感兴趣但是读下去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的无论你对具体的人的这个观点的是可否但是我觉得放在这个大的环境下
它的产生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或者我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书它本身也不是说赞同某一方的观点它其实是在呈现一个围绕着这个词围绕着这一个过程的一个辩论的一个阶段甚至你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各方辩手然后在一个当然他们不一定每个人在回应对方但是你把它编辑在一起你会看到他们之间是有一个互相的呼应的
不过袁老师刚才讲到一个点就是说作为 80 甚至可能一部分 90 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赶上的是一个叫做第二波国学热当然我们说这个第一第二很有可能就是说从改革开放的初期才算起的
因为在之前也有一些类似于对国学的讨论之类的嘛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个浪潮其实我想讲的是我们的听众很多可能对当时所谓的第一波的国学热是不太熟悉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现在一个 20 多岁的比较年轻的朋友他可能他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他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所谓的汉服运动也好或者说电视上播的历史片也好或者说一些书店里也好呃
甚至一些网络上的视频频道也好讲的这些传统文化这样的东西他已经习近为常了但他可能没有经历过一个这些事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年代比如说像在 80 年代的初期他可能一开始有一个共识共识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但是那时候可能就在我看来可能有两种比较显著的观点第一种是我们可以以一种中国传统的东西去反对它
比如说有一些所谓要振兴儒学的人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而可能有另一部分想的是我们要反对这个错误的东西恰好是要彻底的去把所谓的传统里面的东西给去掉这形成了一个在那个年代的一个辩论或者说争论的一个焦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如说我说的第一类人就是要从传统的角度去反对文革
那他可能就会讲你看文革正是毁灭了我们的传统比如说毁灭了我们的节日毁灭了我们的艺术毁灭了我们的文学毁灭了我们的一些其他方方面面的传承伦理还要破坏伦理对伦理包括家庭的伦理包括说那种
所谓的礼仪之类的东西而另一边的人可能就会说这种破坏的力量恰好是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深处的他们之间是没有办法互相分割的所以说我们可能要用另一种东西来把它取代掉而且在当时可能整个中国也有一种需要重建一个身份认同和自信心的一个过程那么那时候也就存在一个如果你要去建立这个认同和信心你是从什么角度去出发的问题
包括当年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什么关于黄河关于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甚至于说在 80 年代也开始出现了那种古装篇这个东西
因为在更早之前拍的一些不管是拍还是说在线下去演的一些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近现代的为主如果你要拍一个古代的王朝时期的那些电视剧就会被认为是立场上有问题或者说你这个创作的思路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而那个过程之后才有了那个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东西在那之前那个习以为常是花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去建构的其实我们在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的讨论的嗯我先回应一下刚才一个是天一的一个问题谈到散文啊
其实这一套书它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散文的选编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家可能谈到散文这个文类的时候总多多少少的有一种想象就是觉得散文它的质地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文风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主题但是我们这一套里面的这个散文呢一般把它称之为叫做大散文
所谓的大散文就是其实它是想要摆脱对于纯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对于文学过去有一个特别所谓的文学性或者说美文抒情性的这一类被认为是散文或者是纯文学
但是這一套的整個的選擇是想要從更多的雜文學或者是從這個大的文學甚至是用中國傳統的這個文章的這個概念來定位更加的合適所以你看到這裡面的選題以後可能你會覺得它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美文或者是從文學的這個東西
當然這裡面我自己覺得比較有意思的問題就是今天大家還會去讀散文嗎在今天的一個新的媒體環境底下大家真的會拿一本這樣的一個散文集來讀嗎這裡面就會涉及到我覺得有一個稍稍尷尬和錯位的地方
就是慢速文化第一套就是慢速文化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推出的時候那時候其實跟整個 80 年代的那樣一種閱讀的習慣還有社會氛圍是比較合拍的它點壓的兩個東西一個是所謂的文化熱大家對
泛文化的東西都很感興趣第二個是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散文熱 80 年代有大量的包括從俞修宇大家很熟悉的俞修宇或者說大量的散文家出來所以正好那一套書它是趕上了這兩波既是散文又是文化但是到了今天到 2023 年的時候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閱讀媒介的環境當中
大家還會去讀或者是憑什麼你會要求大家拿出一本這樣的散文集來讀呢這其實本身是需要打上一個問號的所以這一套序編的推出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它不是順著今天的閱讀趣味或者潮流它有點點懷舊的意味
我會說真的是有比較隆重的懷舊的意味就是它的編選的方式包括它編選的這些文本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就是它是一個錯位的
在某種程度上這樣一種散文的選本是帶有錯位的一個色彩然後剛才竹西談到的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你是 80 後是吧 85 前還是 85 後我 86 的我是 82 的所以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雖然我們主要的這個教育是在 90 年代後但是還經歷了 80 年代的這樣一個風雲那這套書是整個的詩錄裡面是帶有很強的 80 年代的某種
趣味和色彩的 當然你剛才談到說在我們今天看來 80 年代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五四時期的一個重複
大家會認為 80 年代的這樣的一些論證剛才你談到兩種論證比如說我們到底是用一種西化的方式甚至是激進的反傳統的方式來走出文革來找到一條新的方向還是說我們需要回到傳統當中去傳統那去找到一個解藥但是其實
這樣的一個論爭就完全幾乎是五四的時候的這個古今之爭和中興之爭的一個重複一個 2.0 版本在文武層次上是一個重複所以大家會認為 80 年代它其實是跳過了文革跳過了四九然後上接了五四時期它是再一次的一個思想解放
所以裡面的第一波的國學熱的出現它確實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在我的那個導演裡面談到的支持期其實已經有這些東西大家已經吵過一遍了 80 年代又基於新的一種需求又把這些的其實大家的角度能夠想到的角度
或者能够想到的这个对立方都差不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场重复的一场重演当然这场重演里面又有新的一些因素的加入比如说我们的本身对对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
我们看到 80 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界思想界的这样一种分歧包括中国往哪里走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是跟 50 世纪的很多讨论它构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或者说呼应或者说我刚才说的一种重演的一个关系对我刚才想到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在刚刚走出文革的时候的很多文艺作品其实讲的是一个当下的生活
就比如说文革时候的那种什么家庭伦理包括什么回乡的知青这所谓的伤痕文学然后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有那种走向更久远的历史的东西走向一些更传统不光是在人们以杂文散文互相的论争包括在文艺创作甚至说在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东西因为刚才其实袁老师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你作为学者回到老家老家的亲友们会觉得
你上到一个装电视台这样的官方的电视台是对你的权威的身份的对你学者身份的一个认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想到的一个逻辑是至少这一系列论争他们除了主题上的一个变化之外还有另一点就是媒介的变化比如说在巴西我们可能看到发生的人大多数是学者
学者通过在书报上刊文互相呼应的方式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 90 年代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一般的民众他可能渐渐的就从一个聆听者向发声者去转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汉服运动汉服运动的这些发起者他们并不是学者
至少在他们运动的早期的那个阶段他们也从来没有什么登上过电视台去宣扬自己的观点他们其实是借助了像互联网也好像一些新的交流的平台他们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但他的观点很有可能是在前面的那些学者的一些观念互相交织之下而形成的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媒介其实是全然不同的和之前的是不一样的
包括像您刚才讲的这套书你以一套书的方法来回顾一个过去几十年的思想的变化本身在 2023 年已经变成了一种很老派的做法
虽然在 80 年代在报刊上刊文甚至书信那个年代有很多私人的书信来往然后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交流方式但现在的人们显然已经没有再继续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者说使用这样方式概率已经变得非常小了所以这是一个关于这场论争变化当中除了主题的变化它的媒介变化的一个影响而且我认为它由于卷入了更多的我们所谓的一般的人他们不是专门靠学术吃饭的这些人他们不是专门靠学术吃饭的这些人
他们会让这个辩论产生出更多更多元的一些色彩比如说就像我看到的
很多最早开始搞这些所谓汉服运动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城市里的上班族或者是什么大学生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人而他们去想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比那些书斋里的学者要更加激烈而且他们也很有可能是更加行动主义的就是我想完之后我立刻要开始去做这样子所以博学的这个话题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我自己大概可以想到就是
它像一陣大風但是這個風裡面有幾個機制在裡面作用剛才大家比較強調的是當然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它具有很強的草根性的一面就是所謂的民間的這樣的一些他們出於自己的訴求
但是其實國學的這個話題它的敏感性在於我把它分成三個一個是它有眼光向上的你不能不說國學它的幾度的這個所謂的熱起來它跟
国家层面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导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层面我们必须说它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它跟国家跟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指向它的一个关系这是第一个维度就是跟国家政治的这个关系第二个维度是基于我的立场能够看到的说跟学院派的关系它跟象牙塔里面是有关系的因为有吃国学饭的人
所谓考据者也好不管怎么样所以他确实国学也变成一个象牙塔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学术第三个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市场媒体还有民间所以国学所谓的国学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旋风它能够卷起来的
一個原因它有這樣的幾個機制在裡面共同起作用一個是國家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這樣的一個風向第二個是知識分子在中間的一個它往上往下的一個交互的影響第三個是以市場這個市場包括我們談到的出版也好媒體也好甚至是這種
某種社會運動的方式以草堆性的運動的方式在推進的所以這三種機制的交互作用可以說共同形成了從 80 年代一直到可能當下的這樣的幾輪國學熱的背後
都可以看到這三種作用就是所謂的政治的作用還有就是學術的作用和包括引進經濟需求市場的作用甚至我們後面會談到的商業的經濟的這樣一些作用所以它不是某一個單方面的這樣的一種機制能夠掀起這麼大的一個漩渦的是的剛才提到的其實這三種機制裡面兩種都跟這個鬼王城的畢業
无效息息相同就是刚开始知道大家要选这本书的时候我心想哎呀怎么说呢因为就是我从人大毕业嘛然后我是中文系的但是就是一直知道人大的国学院是一个很特别的院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听这个院名说实话刚知道这个名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蹭热独办的院
其实就像这本书里面有文章提就是那个时候零几年的那一波国学跟很多社会事件热点或者那种热搜性的事件是有关的所以当时从一个普通人看来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这帮人就是在
怎么说想营造一种热度然后可能想从中捞钱或者捞名声什么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人大办了一个国学院你就觉得是不是那种中年男人想象中的流行文化的那种感觉就跟现在很多那个出版界老总想办播客一样就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后来进了人大之后然后因为也是因为中文系所以和国学院有一些联系有一些共同的课然后就觉得这个地位更加尴尬了因为
我们会上共同的课但是呢我们又不是一个院但是就是又好像哪里很很相通比如说因为我还算是研究西方文学方向的但如果我是研究比如说文字学或者中国文学或者是文学理论那你就会觉得我好像
是不是应该去国学院就会有这种自我认同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想说那不如我也来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还专门就是我先上了人大国学院的官网然后我就等于说想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学校现在都在干嘛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刚才大家说到古琴嘛然后人大国学院现在是有专门的古琴班的然后就是你只要是在国学院在读你都可以免费学然后有学两年的这么一个机制除此之外有那种不是咱们都想得到的什么中国文学史啊然后那个各种各样和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相关的班之外还有西域语言文学课
就是包括梵文藏文蒙古文满文等等他的这个点就是把国学这个概念放大了就国学不光是尤其是说不光是儒家然后不光是汉族的文化我们应该是说整个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文化都算是国学所以我才怎么说呢我也是看到这个我才意识到原来现在的国学不是
可能一开始想象中的就是最初那个地区上的国学对就这个概念更大了那在这个概念就如果你把国学扩大为所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文化的话那其实就像这书里有文章说那我们当下也是国学的一部分
但当下这个文化又已经包括了一些所谓西学的部分了所以这个概念我感觉它就会变得更加模糊所以我也想就是问问袁老师就对国学这个概念咱们现在一般会怎么去使用它或者是定义它对 去定义它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
並不說我們要給國學一個準確的定義而恰恰可以通過國學的概念的演變來看到就是說它這個概念的形成它背後的這個機制是什麼
在大家给我的讨论提纲里面其实也谈到说我们今天谈国学其实有一些敬意词或者说可以跟他呼唤的词比如说像国粹像国故那我们如果稍微的放长一个时段来看的话其实最早出现的一个词叫做国粹国粹这个词它是大概在清末晚清的时候就出现的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保
保存國粹 那什麼意思?就是搶救保護的這個意思就是一個很急迫的感覺那當時有一個可以說是一個思想很有影響的一個思想的牛派就叫做國粹主義 國粹成為一種主義但是這個國粹主義它是從哪裡來的呢?它其實是受到了日本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但是日本的這個國粹主義的出現呢又跟近代日本的它自己的一個風向的變化有關其實日本的國粹主義它是要對當時的一個全盤的歐化主義來進行一個反撥
一開始日本是所謂要拖亞入歐嘛他是覺得西方的月亮都是圓的所以他要洗刷他甚至想要洗刷自己作為這個亞洲國家的這個身份要擠入到歐美的這樣一個強國當中所以他一開始走的是一個比較徹底的歐化的路線但是在這個歐化發展到一定的極端以後呢就出現了一個反彈
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国粹主义那当时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日本留学对吧像梁启超啊还有一大部分人包括像鲁迅啊他们都在日本留学所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这样一批人呢当然还有包括很多的政治避难者
那他們就受到了日本的這個國粹主義的思潮的影響那為什麼在清末會出現這個國粹主義呢?這個國粹主義又跟當時的一個很重要的清末的就是這個種族運動當時要推翻所謂的滿清的這個統治跟這個種族結合在一起所以國粹在某種程度上又跟這個漢族的光復勾連在一起
所以清末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刊物就叫做《國粹學報》這個《國粹學報》其實就打著這個保存國粹或者說國粹主義的旗號這個《國粹學報》裡面它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者今天我們也稱之為國學大師就是張太炎嘛
張太炎他就提出說那我們為什麼要保存這個國粹呢是要用這個國粹來激勵種姓就是激勵所謂的漢族人這樣一種自尊自強那激勵漢族就是要推翻當時的滿清的統治所以一開始出現的這個詞國粹的這個詞我們明確的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在
很强的这个危机意识底下在晚清的这样一种亡国的危机亡国亡天下的这个危机底下出现了一个带有很强的一种反波性的它是跟这个欧化形成一个很强的张力的一个词那什么时候开始国粹这个词呢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慢慢的这种种族革命的这个色彩就淡了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就叫做国故
那國故這個詞最早是從哪裡來的呢其實就跟張太炎的一本名著叫做《國故論衡》但是真正把這個國故這個詞發揚光大的呢其實是胡適大概在 1920 年代呢胡適他就以胡適為中心吧就掀起了一個叫整理國故的運動所以這時候他對國故就有一個定義這個定義呢就跟剛才
古王曾談到的一個疑惑有關他說什麼叫做國故呢?所謂國故就是在中國的一切的過去的歷史文化都可以稱之為國故 那這個範圍就很廣了就只要是跟中國沾邊的一切過去所有的歷史文化都稱之為國故那這個範圍為什麼說它範圍廣的不僅是廣
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包含了一个它把我们中国过去的传统学术有很强的等级观念的对吧
其實是有經時子極不是所有的學術都是平等的最高的是經然後是史然後是極我們文學是最所謂的極步之學是最底層的那國部這個概念它的一個厲害的地方它不光是要擴大這個範圍它是要打掉這個等級自詢特別是要打掉經的這樣的一個所謂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說
那诗经和民间的一首歌谣是同等的地位像史记或者说杜甫是跟小说家像曹雪芹是同样的地位他就把过去所有的这样一种学术里面的等级秩序他要给颠覆掉了
正義顛覆那其實是對表面上來說它是在維護以保存傳統文化的名義但事實上是對傳統文化內部的一個大的重拳出擊因為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金字塔結構這個金字塔結構不僅是說學問是有等級
更重要是背後的這個倫理秩序是依附於這個學術秩序的所以它事實上是把一個金字塔式的這樣的一個學術的等級秩序給拉平了變成一個攤成一個大餅一樣的所有都是平等的那平等的名義就是所謂的歷史
他用歷史的眼光看過去凡是過去一切的這些東西他就說你發現一顆恆星跟一個很細微的一顆沙子你把一顆大的恆星和一顆沙子看成是同樣的都稱之為國故的時候那就完全雖然都是過去的學術但是這個秩序就發生變化所以剛才廣東誠談到說國學院我們今天的國學院或者說名為國學的東西好像十分的模糊
它的模糊无所不帮而且这里面的这个等级秩序也变得有一些的混乱它变成好像只要跟这个国度相关的甚至跟现代的一些东西也能放进去这就是从最开始的国粹这个带有很强的排斥性的保守的自我整修的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像国户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国学这样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这个中性的概念就变成了一个大的菜篮子
只要你觉得合适的你觉得沾边的都可以往里面扔这就是我们大致的书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今天谈到的国学好像是一个很中性的概念一开始其实是从国粹这样一个很激进的或者是跟欧化相对立的这样一个概念慢慢的演变过来的
这个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大致的一个背景一个介绍吧我看那个国学院官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的介绍说他会覆盖中国语言文学然后中国史和哲学三个学科然后他们说我们主打的是一个融汇贯通就是说我们不是分科之学是那种汇通之学但是呢你在国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可以获得文史双主学位那哲学去哪了
所以我感觉好像它整体虽然说是文史哲咱不分家咱都是一家但更偏文学和历史一些然后相对来讲在哲学这边可能只是一个补充或者是一个那种概论的学习所以国学院的成立就是人大国学院当然是一个特殊的产物啊
但是它其實背後隱含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學的這樣的一個被重新發明的傳統它其實跟西方我們學西方這樣的一種分科體制形成的今天的大學的這個教育它其實有點很難兼容 對吧?它很難放進去 好像是符歌在那裡就是你剛才感覺到的它跟我們今天的文史學科的這樣的一種文史者的劃分
好像有很多重疊的地方 但又不一樣就是說今天的文史則是這樣一個劃分完全是學習西方的這一套分科體制形成的這樣的一個體系那國學它要用一種更加綜合的或者它所強調的這種融貫的方式來接續這個東西但是它很難放到大學體制當中所以我們看到大部分的目前的綜合型大學是沒有一個單獨的國學院的
也没有一个老师说我是研究国学的我们都有比较明确的专业身份对吧甚至我说我是研究文学的而且我还有具体的诗段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所以今天整个的学文学术的发展它大体的方向仍然是往这个专门化专科化的这个方向在急速的发展所以国学的本身它的这样的一种相对混沌的或者整体性的综合型的
他跟我們學習西方的這樣一種分割自學形成的大學體制他至今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很好的一個融合的一個點他仍然是有焦點但是很難就是國學院畢業的學生他去怎麼來找工作呢?他進一步的發展他好像還是要重新要做落到一個專業的背景當中去他還是要被歸進去一個對對對 這是他比較尷尬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在那个我看过程中我发现就是有国学院的老师他说如果按照我们这种分科制度的话那诗经就是文学院去学习的然后我们去探讨它的文体它的艺术特色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它也有比如说它的历史意义还有它的哲学意义所以在国学院就是可以综合起来研究然后我当时看到这我就想起我当时因为我为了研究生学哲学我去修了西方哲学史
然后就关于柏拉图这个人那个文学院的老师和哲学院的老师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比如像文学院的老师就会觉得他的那些比喻很优美然后或者很有创意但哲学院的老师就会说你用比喻来讲哲学等于你没说就是你说了一个根本说不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其他学科在很多学科都
就是如果要是你能融合起来能不能把学科打通去看待会很有帮助对你刚才谈到一个特别对的一个地方就是确实分科资学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些经典无论是四季也好四季也好
如果從我們現代學科意義上去看那我們看到的只是它的一個切面嗯很單一對我們只敢涉及它跟我們專業背景相關的那一面但事實上它可能是一個整體性的一個學問甚至它是跟人的這個修養修身相關的一個學問
所以他需要用一个更加综合的整体的眼光去看待他这确实是用国学的这样的一种相对融贯综合性的这个眼光来看待过去的这些经典他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能够比较整全的去读整全的去理解这些思路而不是用文学历史哲学这样的一种把它切分开的方式来去读书来去理解里面所传授的这些信息其实
其实刚才那个鬼王城一上来就问老师国学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录不知道多少期了因为我当时就想说就是国学是什么你这个问题可能到往后都没有办法有定义嘛包括老师也说这更多还是我们在探究其中变化的过程对不对
然后我在做功课就是我在写提纲之后的这几天我其实发现了我中间漏掉了一个点就是老师您在您的导读里面引用了那个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国学从刊序然后里面提到他说这个
学不应该有新旧不应该有中西不应该有有用无用然后我在读他全文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点非常有趣他就说中国今日是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然后他就还说就是中国都没有几个这种能够弄清楚中国学术的人更别谈这些能了解西方学术的人就是说他当时的这个提出那一系列的这个观点的一个非常基础的点就在于
他认为中国整体的学术都是没有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这种张力这个前提和他包括他后来的那种探讨实际问题的这个张力是在后来其他的这些更加现代的一个作者的文章里面也看到了其实很多人他是在不同的基准点上说的一方面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就是中国已经吸纳了足够多的
西方学说然后他也有一定基础的这个中国学说于是来探讨这个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哪个更好或者说这个国学的有这种可能国族意义的价值在哪里等等然后另外一部分人他可能更偏向于那个王国伟刚才提到那个观点他就说
中国这个问题就是不论你中学西学都没学好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读了这篇文章还是作为一个很关键的钥匙吧可以解开一些这本书里面剩下的就是现代作者们提到的一点就是大家谈论国学的时候
这个国和学这两个字的关系究竟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有我的理解就是王国维在这个国学重刊系里面提到他更多的是可能是讲中国人做的学他并没有说这个学跟你这个国家的一些传统或者这个国境文化有那么紧密的绑定他可能更多一个模糊的就是说你这些所有可以自称为中国人的或者有这个标签上的这些人他们做的学问
而这一点其实包括就是国和学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真正看到这些书里面收录的散文里面所有的作者就无论他对这个是多么支持或者批判的态度他都没有说真正的把这个细细的给拆解开来当然你从他们观点里面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持了这个什么观点就是这个国跟学的关系这个国是什么是具体的人呢还是他一个更加抽象的东西
而他这个学他是一个具体的某种知识或者刚才提到的他可能有一种这种等级的一个东西在这里面一个等级体系在里面等等所以我觉得拿着这样一个见解进去读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对王国荣的那句话特别的超前
特别的超前刚才你说它是一把钥匙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觉得那所以我在血液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他谈到说学无古今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但是当他在说无的时候恰恰是因为血陷入呢我们说的这一系列的有用无用中西古今的争辩当中所以王沪一开始他要鹤破这个东西或者说用刚才你说的那个词就是要结绑
他要强调的是学的这种超然性超然于一时一地的这样的一些纷争它具有一种终极的价值但是有趣的这个张力正在于此就是王国瑜树了一个很高的标的他说学可以挣脱这些纷纷云云的论证这一百多年的这些争吵但是呢
学又始终无法征途啊这是这恰是这个问题有意思的地方如果学所谓的学它真的能够成为超然一时一地的这样一个纯粹知学的话可能它的
這個魅力這也從王貴自己的命運我們能看得很清楚對吧那如果大家對王貴稍微有點了解一開始他是支持文學他的人間詞化我想大家都讀過人間詞化包括他的《紅樓夢》的這個研究然後他要放棄文學他要去轉哲學受到西方哲學的這樣一個影響但是他最後折入的包括他對於古文字的這樣的一個
等等等等所谓更加传统的这些学术当中最后当然他的这个制成那为什么是制成这就说明至少在 20 世纪的学术和学人都没办法做到纯粹他所谓的纯粹的
超脫於這些現實的論爭或者說倫理的紛爭當中他的製程就是他用他的這個死恰恰證明了 20 世紀的學術他的最後的這樣一種悲劇性的命運就是他沒辦法跟國他所認定的這個國他沒辦法跟他所認定的某種文化認同真正的解開所以最後只能兩個東西糾纏在一起糾纏得越來越緊然後最後
無解的時候只能用死來證明這個學無法跟國無法雖然他認同的那個國未必是所謂的民國當時大家應該知道他對於清朝的這樣的一種認同但是我覺得王國爺的他既能說出那樣的話來標示出所謂的學的這樣一種獨立自主超人的一面但是他自己的這樣的一個命名他的這樣的一個最後的選擇
恰恰证明了至少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直到我们今天学没办法超然于国甚至被他跟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十分十分复杂难解的一个关系所以王贵最后才会以自己的志成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解答
這是我覺得有意思的一個地方就是說他這麼早就提出了學古今中西有用無用但是最後他的這個命運他的選擇又證明了這些紛爭又會改變或者是會把這個學的這個純粹性在某種程度上消解掉這中間的這個複雜的關係是我們討論國學臣服所以我用了一個雖然大家
都關注國學這個概念其實我覺得我用的那個臣服這個是這一個詞想要表明的並不僅僅是說國學熱它是一種見發性的一會冷一會熱而是確實它會影響
学人甚至是整个国族的某种臣服所以我用的这个臣服这个词背后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别的一些暗示的一些意思对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个臣服一个词的这个重要性的话我一下就想到就是说他给这个国学赋予了一种
更加那种客体性的感觉吗它就是一个在我们现在身外的一个物件而并不是一个非常本质主义的一个不变的一个道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这个书里面收录的文章里面探讨的一个关键点吧就是关于所谓传统就是包括中国文化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国学它跟一些词有这种敬意的意思然后我当时在提纲里面我也自己在想就是说它跟哪些我们可能虽然不会这样表达我们
不会说这两个词是近义词但其实我们在说国学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其中一个关键的两个词就对我来说就比如说什么中国文化或者传统文化这种东西就大概一谈起来这可能感觉在意义上是分开的但我觉得实则是非常绑定的紧密的东西何谓中国文化何谓传统文化这些也是就是刚才提到的非常模糊的概念非常复杂的概念你没有办法去很清晰的画这个边界的
然而就是有一些可能学者他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中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即使你有这么多年的历史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变迁你还是可以从中间拉出一条线来然后一直说到他他也许在这个五四期间发生了某种断裂或者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或者整个解放后发生了一个断裂之后重新又续上了也也有一方是这样一个
概念另外一方就是可能你认为就说这个概念一直是在变化的他是由这个当下的当权者
他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他结合了现存现在条件的一些因素把它进行一个柔和然后他当时的留下了一些东西在之后又慢慢的沉积到下一代或者就是下一个这种有集权的这样一个对意识形态进行更大管控的时代然后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再进行一次重塑所以我也是好奇就是借用一下这种吸血的概念就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你要说国学或者这种
所谓的文化嘛可以就是用意识形态来带我来看更加客观的一个词汇就是意识形态来作为一个代表然后他中间的这个此消彼长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的话也许也可以更方便很多人去看清楚就是说他这个东西的运作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有些人可能给这样一个带了国字的一系列词汇加上一种这种情感连接之后你很难再去客观的去
把自己从情感连接中间剥离出来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你也许道理上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这个情感连接非常受支配于他的对
对举个例子如果你说我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天经地义的东西那别人就很难去说它对还是不对了所以既然有国这个概念就有所谓的非国或者说西因为其实最早的国这个概念是周围西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所以有在很多人看来因为当然首先我们要承认国学的概念是一直在变的而国这个概念首先它就有涉及到一个对立面的问题有很多人的观点他可能认为是国和西可以各管各的
或者可以存在一种竞争性交融性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其实认为就是要国就不能有西就类似于说最近的这好多年可能二三十年吧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在医学这个问题上就呈现出一种非常这样意识形态强烈的一个倾向就是你一定要说中医好
或者说你说中医不好就是不爱国你会看到但这种人也不是很多了但是你会看到有类似这样的一种声音去他一定要把这个中和西这两个概念之间做一个二分的对立当然他那个逻辑其实很容易戳破的嘛比如说那你说数学有中国数学或者说西洋数学物理学有中国物理学或者
西洋物理学好像也没有但是在医学或者文学或者哲学这样的一些方面他可能就会试图去营造一个其实是把它作为一种防御的工具了嗯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陈平原老师的那本书陈平原老师的那篇文章我就觉得还就是他很犀利就是他从那个要把国学分为专门搞个学科这一点入手嘛然后他说你硬要给他设学科设学位其实你反而是用西学的逻辑在套国学然后他也说国学就是被西学逼出来的所以是一种防御性的词语对但是呢就如果硬要把
国学和西学做切割其实也做不到然后就我看他这篇文章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用急着分中西或者分你我就是他这篇文章我觉得如果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可能就是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
特别要选陈老师那一篇就是他的《国学新视野》的那一篇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学它的产生其实就是跟吸血照镜子相当于是通过吸血这个镜子照出来所以国学它是一个用我们学界的话它是一个被发现的
被发明的一个传统它并不是古于有知的东西它其实恰恰是近现代通过跟吸血的这样一个对照甚至是用吸血的方法或者说当时称之为叫做科学方法的这样的一种新科学重新来发明出来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学问所以
所以陈老师才会说他说这个国学是被西学倒逼出来的甚至国学的这个形态它的体格虽然它打着国但是它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体系性的方式这种看待学术的方式其实就是西学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从国学诞生之初
他已经是通过吸血正面镜子来反照出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自我的这个形象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分只是说后来的这样的一种把它切割开以后的二分化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很多的误解都在于此那个龙厚力老师那篇文章他也说就是这一度的纠结点是在于要怎么让国学靠上科学
等于你要施以长计以制宜那种感觉你要用他们的方法来接近他们然后打败他们所以连考据啊然后甚至那种迅孤的感觉都要和科学挂钩然后在这个背后罗老师也说是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的我猜一句罗宏林其实就是很有名的近代史学者罗志田
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在讀書上用的一個筆名其實就是羅志田老師然後羅志田老師他其實有一本專著我今天也帶過來他就叫做國家與學術然後是親近民族關於國學的思想論證這是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關於就是民國時期的關於國學的一系列討論的比較系統的一本專書
嗯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看罗老师的这本书吧嗯对对对刚才其实葛王城在讲那个陈平安老师那个观点的时候我已经其实把那个罗老师的文章已经翻出来了因为我也正想讲为什么就是说到这个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对他这个文章本身标题就是关于科学的嘛他讲这个国学与赛先生嘛但是里面还提到一点就是而且我觉得整个集子里面就是其他作者都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他在里面点出了就是说当时就是新文化运动期间
一些对于国学的这个反对者他其中引用鲁迅嘛就是鲁迅提出一个点就在于就是当时的就是中国的很多这种研究国学的一些可能比较保守的这些学者都在读这个过去的这种更偏向儒家这种典籍
然而西方的这些所谓的汉学家已经在中国的各个地方研究他们的文物或者直接就拿走了这个关键点鲁迅当时是观察到了的包括汉学作为一个概念也一直是作为一个非常没有关系的一个概念似乎
存在这个国学的这个范围之外的我在这个提纲里面也把这个汉学标注出来的一个点就在于当我第一次认识到汉学这个概念存在的时候我所谓知道什么叫做欧洲的这种汉学家他们当时来中国的一些历史背景等等我就想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研究的那些内容很少是被中国的学者似乎作为他们学术成果的一部分或者来借鉴他们的
然后回到这个国学这一点也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国学院里面的运作形式如何但是我觉得这些西方学者从可能殖民时代的到现在的一些整个风气当然发生了一个变化到现在的一些研究中国历史这些学者的话他们的很多内容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论都是非常值得阅读的
在这个层面上我我似乎就是觉得无论是中国的这个文化界还是想借对这个的可能说跟他们的对话都是比较少的就是我一直都很好奇这一点就是汉学似乎一直都是个非常脱离的一个概念
就西方汉学不是日本汉学我稍稍插一下就是刚才谈到这个汉学的这个问题可能跟天一说的不完全一样就是汉学刚才你谈到的特别是法国巴黎的对吧就是欧洲的这个脑派的汉学它其实对民国的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刺激这个刺激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陈元这样的人就是当时中国学术特别是文史哲学他受到
西方汉学比如说东皇学的这样一个刺激东皇学的刺激以后就感觉说这是中国自己的材料中国自己的宝贝怎么都被别人的研究的这个东西呢而且当时很多学者要去大英博物馆或者去法国的要去很多地方才能看到这些文物所以大致我觉得从清末特别是到了抗战时期史学包括很多学科的这个
發展的一個內在的他們要競爭的對象就是漢學他覺得說漢學的中心不能雖然現在的中心變成了巴黎甚至變成了東京像羅振宇和王國威就會發現在日本有大量的學者像那個湖南還包括很多人他們對於中國對
所以這些學者法國的這些漢學家還包括法國德國還有日本的這些漢學家他們其實對同時代的中國學者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和刺激當時歷史學家成員就說了一句話他說每當法國漢學家發表一篇文章他就感覺有一個炸彈就落到了自己的書桌上
他們有很強的這樣一個急迫感這種競爭的一個心理這是漢學一方面就是對中國產生了這樣一個巨大的這個壓力以後中國的學者他其實包括王國維他轉向中國的這些小學文字哲學他其實一個巨大的就是受到了日本的漢學的這樣的一個刺激
所以汉学对民国学术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同时对他们产生了很深很深的心理上的刺激就觉得要把这个汉学的中心夺回来这是富士年他们当时在 30 年代在成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在他们的成立的宣言里面就谈到的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要跟这些汉学家进行竞争然后中国的学术的正宗必须在中国
而不是在巴黎不能是在東京這是他們的一個追趕的這樣的一個心態所以確實漢學跟國學之間的關係十分的緊張但是這個關係既有競爭的關係也有這樣一個很深的一個刺激是一個強烈的在民國時期這兩批學者是一種針線恐後的無論在材料的爭奪還是在研究方法的推進還是在具體問題的解決都在這個賽跑的過程中
过程当中可以说其实在 80 年代曾经就有过一个运动嘛就是说那个欧美的探险家要来中国什么登山啊什么漂流啊什么做一些穿越无人区啊然后中国就有很多人说呃
我们宁愿牺牲也不能让他们成为这个第一个人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心理模式是一样的虽然他可能一个是学术层面的一个可能是自然层面的都是探险对吧都学术的探险跟这个自然的探险征服做探险的工作是一样的而且中国人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在全世界各地来说是对
执着程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的学术的重心一定要在我们这里而其他的话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埃及人其实你看搞埃及学的好多都是欧洲人然后但是好像埃及人没有那么强烈的动机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古埃及的学术中心必须在开罗必须在埃及的某个机构里面包括其他的类似的
有的比较长的文明史的国家里面似乎中国在这方面是最执着的但是可能也跟晚清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的局势是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甚至于说您刚才讲到的 30 年代的中国成立一些研究中国的什么历史语言文学这样的一些
本身也跟当时的那个外界的这个侵略和这个整个国际形势的紧张有着直接的关系包括当年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经常看那些科普书上就会讲说当时的那些考古学家比如说拿着一箱甲骨或者拿着一箱什么北京人什么山顶洞人之类的那个上古就是远古人
时期的人类化石装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在那个战争期间纵横几千里然后在全国到处躲避这个战争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留给后世的人可能作为一个小孩来讲你觉得它是一个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时代背景的包括像你前面讲的说国学可能就有一种
不光他在学术研究的这个方式上我们要比别人研究的更好或者说我们要产出的成果要比他好另外他从结果本身也有一个竞争性比如说我要证明我们的文化是最古老的最优秀的我们有的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包括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视频是介绍一个博物馆的那个博主那个介绍者就在说
说你看这一样文物就证明了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某某某某的古文明他可能没有很有意思的去说这个东西但是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他的整个的思想的模式以至于说他一说就自然而然的说到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是不管从研究的方法还是从研究的结果上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竞争的心态或者说一个防守的心态因为竞争可能还是说我要语言比强
他那个还是更多的是一个我要防止别人来打败我的这么一个一个状态包括您刚才也讲了嘛说日本学者经常研究中国史当时就说啊你看你们日本人研究中国史就是为了否定我们的伟大或者说否定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蛮猛的问题对吧
他们很多人都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就和现在的很多中国学者去骂美国人研究清史是一个道理所以他这里面的这种学术之外的或者说对于现实问题的关切其实非常强烈但他可能又不会说出来他又不会直接写在里面
我觉得那接下来可以就延续的这个时代背景的一个探讨啊就是回到近几年的一系列或者近 20 年的这种国学热因为我们刚才其实很多的这个讨论还是在基于有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产生的一些争端就是那个时候包括刚才那个袁老师也讲过就是从 90 年代起的这一第一轮这个国学热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的一个延续
然而呢在这个零几年之后的这个我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个就是这两个时间节点都很有趣啊就是首先就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国学热是在这个 93 年左右开始的然后 00 年后的这个国学热是在这个 0506 年开始的但是这两个时间段都是跟这个中国当时的那种
经济发展或者说国际化的一个节点是非常吻合的就是 92 年的时候在南巡之后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
然后是在 2000 年在深奥包括你这个进入 WTO 之后包括这个经济发展这两轮国学热都是在怎么说呢也就是应和了当时那个经济的一个潮流包括他这种国际化的潮流也有学者在那个文章里面也点出来了嘛就说他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国学的设立他的一个这个外部因素就是在于
这是一个对外推广的一个工具它是可以把它或者说专门谈孔子的话就是把孔子作为这样一个象征可以拿到全世界各地去设立这个学院是有这样一个文化输出的意义在这里的所以我也就是很好奇就是看这是第二轮国学热就是我和永安城小时候经历的那个国学热对就是他们的国学热 95 后了都要
延续到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对于那这个 90 年代的那些争论其实对于普通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已经非常陌生了但是就是对于就是刚才又回到那几个百家讲坛里面的人物或者一些经典的一些书目那些东西对于大家还是很熟悉的我现在也看到就是包括播客平台上面就是在播客在国内兴起之前的
包括也现在也是就是在那些各种音频平台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类
还是国学类的东西无论是讲历史还是讲这种典籍他们的收听率他们的收听量仍然是非常高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只不过他们的这个主讲人可能有时候就脱离了这个夏娅塔他们也许没有那样一个什么在职教授的这样一个光环在这里或者这样一个位置在这里他们也许是业余的学者甚至都是这样其实你说的这个让我特别想起了我插一句就是特别想起了那个以前
你去很多城市的小区里面或者街道上你都经常能看到什么国学培训之类的机构里面很多人可能我相信也不是职业的学者他培训的东西可能也五花八门可能也有什么传统文学也有什么诗词情气书画什么的
所以这就也展示出这个概念的那个边界的非常的可延展性对所以我也好奇就是袁老师您对就是现在就是从那个时代相当于国学的一个彻底商业化之后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发展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其實我特別想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這個題目就是說我編這個選本的時候主要還是從思想文化但事實上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們如果把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行一種文化研究或者是我特別想了解的是受到 90 年代或者是 2000 年以後的這個國學社
其實有的時候改變了很多人我前不久看了一個材料就是那些讀經的孩子就是有些家庭就直接把孩子從正常的學校教育裡面拉出來然後把他們送到讀經班而且是一種封閉式的然後最後這些孩子他們的命運是什麼樣的他們是如何回歸社會可能有些人
嗯 了解國學 學國學只是作為他生活的一些點綴但是有的時候這些國學熱發燒到什麼程度它可能會改變很多人啊 所以我在想其實國學熱的這個題目不僅是把它看成是一個知識界的一個什麼思想論爭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層面我們其實真的應該去好好的做一個社會學的調查
社会学的调查包括刚才谈到的读经班这些机构他们是哪些人然后这些人里面他影响了什么样的家庭那甚至我们可以去追访那些就是曾经参加过这些读经班的孩子他们最后他们的整个的我觉得人生命运可能都改变了
所以我自己想到的一个工作就是我觉得应该把国学社的这个东西从一个话题变成一个文化研究包括媒体研究刚才你谈到了媒介研究特别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题目
他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访谈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追踪性的一个调查这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看到一个思想的这个热潮起来以后他对这个社会的机体对这些个体的细胞他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我自己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
可以找同学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才能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当然整个 2000 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国学热最基本的几个背景其实刚才已经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一个背景当然是这个经济的它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的市场化所导致的这种消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兴起
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这样的一个全球化中国要走出去那中国要走出去的背后就有一个你什么样的形象走出去对吧这个中国不仅是说是一个富强的中国中国的崛起的叙事里面它一方面它是要说重新回到一个富强富强是它的一个目的那第二个是
那當這個中國重新開始開口說話的時候我們今天經常說的話講好中國故事這是一個經常談的一個話為什麼要說講好中國故事呢這裡面就涉及到中國對於自己的文化形象的一個重新的定位
而且这个文化形象它需要是一个连贯的需要是一个从孔夫子就开始讲下来从孔夫子讲到鲁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怎么把这个故事才能讲完整那事实上这个故事中间有很多的锻炼但怎么把它连接起来
另外一個我覺得值得可以關注的現象就是近些年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考古的這個專業十分的紅火是的所謂的考古的背後就是對於中華民族的叫做探員工程我們的文化的源頭到哪裡來不僅是專業很多人對這個專業有很多的想像包括大家去各種各樣的博物館我自己也經常看
也特別喜歡看這種考古的這種現場的一些紀錄啊 視頻啊 包括三星堆啊等等那對於這個會發現大家對文化源頭文化源頭的這個高度的興趣包括對於夏商周的這個斷代工程的這樣一個國家力量的這個投入所有的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徵後就是我們希望講述一個有頭有尾的年貫的一個敘事
這個敘事最後是能夠落實到這個復興落實到一個完整的中國的文化的形象這個文化的形象是曾經被打碎的這就是在五四時期其實是我們自己把這個形象倒碎以後現在一片一片的要把這些文化的碎片重新拼接起來所以背後的心態我們可以談很多的事件很多的現象但背後的心態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中國人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活著就是我們今天怎麼做中國人的問題剛才談到一個很有意思就是說不僅國血要打上引號
中國的本身也要打上一套如果說中國它不只是一個疆域不只是一個政治的共同體化那它作為一個文化的共同體那怎麼來定義它?怎麼來揉合不同的傳統?悠久的傳統 還有包括五世以來的傳統還有包括共產主義的這樣的一個歷史這些東西怎麼把它
聂和在一起 陳老師那篇文章裡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詞他叫做血脈貫通 對吧所謂的這個把中國的講順了 講通了從頭到尾的 全尾全虛的一個故事
這是我們今天最大的一個教理講不通是因為中間有很多我們自身的一個自我否定自我懷疑所以這背後國際的背後有很複雜的這樣一個心態這個心態是在兩極要麼是高度自卑的要麼是自我膨脹的但是怎麼找到一個比較平和的心態
講好這個故事其實是我們今天還沒有找準的一個基調有的時候要麼是太過於自我貶低有的時候過於的高亢這是一個就是陰雕不准這個背後當然跟我們談到的整個的二十世紀的這個歷史有巨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在谈这个国学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很容易拍桌子很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就是背后的刚才谈到一个特别好的词就是什么这种情感连接对吧很容易触动大家对于国的这样的一个每个人在心里面引起的不同的这样一种情感反应
就很难像王国瑜说的这样把这些价值的层面全部剥离开来我们就事论事的谈不可能每个人对这些东西都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情感反应这也是我们除了作为学者之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很朴素的一些反应都会被放在
放在這裡 但是剛才我談到的我覺得我談的第一個特別的重要就是我真的希望有人來做這樣的一種社會田野調查來把國學不僅是看成是一個思想論證而是說它作為一個從媒體的層面然後再到這些機構民間的機構的層面然後進而影響了千千萬萬的家庭
或者說甚至改變了某些人的命運從這個層面來梳理這幾次國學熱說產生的社會影響我覺得會比我們今天光看這些文章裡面的這些觀點可能更有意思因為我們深入到這裡面的這些文章它們基本上都是一些思想者他們的一些觀點 他們的意見和觀察
但事实上比较少有社会学层面的一种描述细描深描甚至是实际的调查
我覺得需要把這兩方面把觀點意見和實際的社會調查調研放在一起才能很好的呈現就是這 40 年來的幾度國學熱它實際的產生的影響是什麼我看石友宇老師他那篇文章他也指出就是說他覺得國學熱是出於一種焦慮嘛就我們覺得好像已經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已经就是不熟悉到一个无法忍受的程度了然后这就让我想到近几年的那种对洋节的抵制然后就说要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在就是近十年才开始提的我觉得在之前也没有那么有那么
抵抗或那么抵制排他性吧我觉得认为是两个部分一个是重新开始过自己的节再有一个就是不能过别人的节这两个事还是有先有后的
因为我其实我小时候记得我父母还跟我说过说他们在文革的时候会碰到要过一个革命化的节日这样的一种提倡就是说你不能按那种传统的方式比如过春节你不能去放鞭炮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如何革命化的过春节就是去劳动但是到了 80 年代又重新恢复了这个过程就是比如说一些民俗活动一些祭祖祭神一些什么庙会这样的东西开始
开始出现但他还是损失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在华北地方的这些庙会肯定是把里面的那个地方性的神灵崇拜这个色彩给压制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但他是可以恢复一个就是自己的节日包括后来设那个假期就是你看以前的那个假期是没有什么中秋端午这些清明这些假期这些假期是一个一个后来被加上去的但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一个反阳节的活动因为一开始其实
因为洋节在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获得过官方地位因为政府从来也不在洋节放假洋节其实是一些自己觉得好玩比如说圣诞节不放假但是圣诞节那天可以比如说约几个朋友去玩或者去参加一些活动之类的
而且它也不一定和西方文化和西方宗教有关系但是对它的反对其实从我的观测来看至少新世纪以来就一直有这个论辩但是在新世纪的前几年这个论辩一直停留在嘴上的就是有人说不该过
有人说该过这些人可能是些知识分子在那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通过那种传统的方式在报纸啊或者这些地方去发文章当那个时候有些文章已经可以上网了然后这个等他这个东西再过到比如说一几年尤其最近几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从纯粹的打嘴仗演化到了一个真实的行动就是真的会有人去说你不应该过那个节是
甚至你会看到有一些机构会发通知像有些学校就会说通知学生说不能过感恩节为什么因为感恩节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然后这种东西就会出现这个东西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上一波的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波文化热里面还没有存在这个概念嗯
就他更多的是振兴自己而排斥他人的这个东西至少没有那么显性的我其实听到那个袁老师说的就是关于社会学研调研的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您也刚才提到我们可能或者学术界吧目前的这个主要学术界他都在关注这种连续性的构建他要把这个一个完整的东西给弄出来
当然我就是回到那个雷锋塔的倒掉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总喜欢臭整嘛但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但是在世界各地他们包括现在大家经常也在说比如说国际的各个地方的这种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等等但是也不完全是这种保守主义而我更多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拒绝
某种断裂的存在或者没有去正视一些这种断裂我觉得就是如果回到这种西方的一些理论西方在我觉得现代主义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现在没有那么显著就在现代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 21 世纪初的上半叶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所面对的对于很多人当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弥合的断裂
因为这是个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太惨重了他们没有办法就说这个时候西方文明是个完整的文明因为它已经到达这种极端毁灭的境界于是说我们要在这个毁灭的状态中如何重新建立起来
而这让我想象了一个就是近些年嘛在北美的另外一种研究他研究的是什么就是研究一个印第安人的习俗就是印第安人有一个所谓叫做 ghost dance 的习俗就是鬼舞的一个习俗嗯
这个习俗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印第安人的习俗就不是说他们是在殖民时代之前就有了这样一个风俗而是呢它是产生于就是在北美印第安人被彻底基本上被消灭之后剩下的那部分幸存者们他们在 19 世纪末形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高度仪式化的一个表现一种表演它继承了就很多各种各样元素他们自己的这种看上去对于外部人观察者来说看似这种古老或者是传统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完全重新构建的一个传统而它存在的意义又跟他们之前过去的那种文化习俗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传统它是基于一种种族灭绝的这种伤痛在这个基础之上在建立起来
包括就是刚才提到回到欧洲的话欧洲的一些学术的基准也是在经历过世界大战这种彻底的这种灾难之后它重新建立起来的
而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们能够有一部分人能够去建立这种东西或者说尝试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去正视一个自己的现状就是对于可能一些当时的德国的哲学家来说二战后的德国的哲学家来说就是说原来的那个德意志已经没有办法再延续了读多少海德格尔你都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东西延续下去了我们必须要做个新东西
或者对于当时一些北美印第安人来说我们没有在现在这个条件下没有办法去夺回我们自己的土地了我们人也死了差不多了你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你要必须要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构建而我觉得至少这种思路在目前的这种在这个主流的学界当然是不存在的可能在一些小的一个角落存在可能对于一些
那种民俗的角度的有些学者他可能是有这样一个认为的他比如说从一个放眼的角度或者说这种文化角度但是即使是那些学者他们也在讲究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东西先保存下来我们要去保留一个我们以为完整的东西但是也许这个过程已经无法进行了所以说在各个层面我觉得在
这是个人浅见就是在中国的学界大家都没有可能做好准备去或者没有条件去真正的正视就是说在清朝或者甚至在晚清到现在这么长的 100 多年的时间里面已经产生了足够大的断裂产生足够多的或者不是断裂就是破碎让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把它拼起来了这时候该怎么办我就觉得这种问题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那我觉得像在最后一部分是最后一部分吧就是葛剑雄老师的那篇文章他就说我们要传承嘛我们就首先要传嘛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先留下来再说你甭管它好坏你甭管它是有用没用甚至是怎么样的你先留下来然后我们在成的时候再选择比如说适合现在的或者适合我们对未来的预期的然后或者是有创新的去继承去发扬就可能这是
我觉得你要说接受中国文化已经有那么大的一个断裂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意见会有不一样可能也普遍来讲比较难以接受因为咱们不一直说是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完全断过断过的
我不用断裂这个我还是觉得破碎比较好就是你现在就在我看来你现在留下的东西不同的碎片它有不同的脉络可以连连续到过去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很好地把它拼凑出来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你原来的那种封建的一些结构你已经就丧失了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背景不一样了对啊就所以说到今天吧你在受到这种西方文化的冲击你受到了这种到现在算起来
快 30 年的这样一个上 40 年的这样一个市场化的这个冲击中间东西太多改变了不是说就是我当然不排除就是很多人包括刚才主席也提到就是可能反对或者国家城也提到反对杨洁或者什么排斥洋传统的一些人等等就是这些人存在并不代表着他们这个任务最终能够完成
就是他们的手段也许会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保守主义抬头的国家也产生这种问题就是他们当权了之后他们也就遇到了一个困境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去就比如说一个高度宗教化的国家这种什么一个天主教国家或者是伊斯兰教国家他没有办法真的去我说我要回到那个时代去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他还是要去跟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族群之间要以一个不同的方式打交道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对他这个哲学上进行一种妥协然后这个东西当然就跟他们最初所声称要复原的一个东西已经截然不同了
但是我有一点点是觉得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在研究古代的文学也好历史也好或哲学也好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孔子并不是说他说的每句话我都要照做或者他说的每句话都是
天理我都要就是很全盘的接受就是他很多话有他当时的局限性在他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他自己的甚至是政治立场当中我们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对现在来说还是要找一些适合我们现在背景的东西去他可能会有启发但这个启发就是一些
就比如说像书里我忘了哪篇文章也举到一个例子就父母再不远游嘛就你这句话放在当时小农经济然后医学也不发达交通也不发达的情况下你如果离开了父母那可能一个是你父母生了病或有事情你没有办法立刻照顾他然后你们之间的交流啊交通也都不够顺畅但是放在现在呢你要是说父母再不远游那哪都别去了对吧所以它是有一种
就是在方法论上是可以妥协的但它背后的精神其实是希望你能关心你的父母你能感恩你的父母它是一种这样的精神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传承的一定不是一种很物质层面的东西我感觉还是精神当然这个精神可能是全世界共通的可能不光只有中国有但是它是一种就是更思想层面的事情
我刚才意识到我们已经聊了快两个小时闲起来会比较费力是没有没有那是姚天一的事情
因为刚才古王城一提到这个孔子的事情就是让我想起来我们其实没有谈到就这个本书的这个编撰的这个结构里面有一部分其实就专门在讲这个儒家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谈到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话题真的很大你国学就确实儒家的东西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共结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时代是非常核心的一部分所以这次可能因为时间
不能太久所以没办法继续细聊所以也非常非常感谢袁老师能够抽出时间来跟我们来分享关于这本书的包括这本书背后这些字里行间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的对这方面的感谢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看的一点就是关于一个问题可能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就比如说像我在开头也说我觉得国学有一度热是那种靠炒作出来的然后有些学者呢就是持比较负面的态度然后但有一些学者就是觉得说那这就是人人都参与会让这个话题就是让大家更有参与感也更有助于大家去思考所以就是好像你对一个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想法就很有意思
我做一個小小的補充其實也是這個提倡裡面最後談到的兩個問題我覺得都很有意思就是說首先我自己其實我離國學當然我對這個話題感興趣但是我不是這個國學的這個領域中人我自己的一個定位我是一個門外漢
雖然我的研究跟國學沾邊但是我不是國學裡面的某一家某一派那這是因為我是一個門外漢所以我在選這些的時候我不帶有門戶之見前兩天我把這個書寄給我的一個師兄他覺得特別有意思他說你這個編排第一個是紀憲林先生那第二個接著是王小波
他說這個中間的跌宕起伏有點大就是說你選的這個膽子有點就是說這個編排的方式如果是其中的任何的一派看了可能都不舒服都覺得漏了很多或者都覺得有些東西不該進來那正是因為我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站在外面的一個我就可以把這種他們爭吵的或者眾生喧嘩的這樣的一個
的這個東西都納進來 按照我的這個眼光這是第一個我要特別要強調的一個地方然後其實這個最後談到一個小的話題就是說這個裡面有哪些話題或者文章沒有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收錄我這次看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個小的補充其實跟我的這個目錄呢 只有一篇區別這個區別就是其實我本來選了李寗老師的一篇文章
他的那个上家狗谈红纸的正好可以回应大家谈的这个问题首先我很喜欢李云老师的文章因为他的文章都不是那种高头奖章都是大白话他写的很直接很直路然后上家狗的这一篇我觉得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选入呢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刚才大家最后谈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谈孔子对吧绝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我们要去像小学家那样考证这个字那个字或者怎么样子而是怎么读这些论语或者读孔子感觉到很亲切甚至感觉到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老者所以林老师说孔子把他说成是一个上家犬或者是上家狗他其实有很强的一个自我投射
他的意思是孔子在当年七七哗哗四处奔走想要传销自己的学说但是没有人买他的上他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宿命啊知识分子就是最后变成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人然后他是精神上的一个流浪者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上加权他的这种读法是我特别欣赏的
就是其實是針對自己所困擾的問題和困惑你去經典裡面尋找某種回答或者是回聲當然我放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錢理群老師關於李寅老師的這個商家選擇他的一個回應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作為沒有收錄李寅老師那篇文章的一個補充吧所以我覺得正好可以回到就是我們
谈到的其实里面的这个书的四个部分呢各有功能第一个是作为这个国学热他作为一个现象或者这个事件还有很多的真硬性的声音第二个就谈到国学里面可能最主脉的儒家传统还有包括孔子的问题第三个
是談這個過去現在將來或者是我們今天談到的現代它如何既是斷裂的又要追求某種連續性最後是回到就是武士跟國學這樣的一個形成張力的一個問題因為武士本身是好像是國學的一個對立面但是它又是這個問題的一個麻煩的一個製造者所以
这本小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未必是说所有的文章都进来了但是它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不是某一家某一派的某一个固定观点的而是不同立场的一种冲突因为国学它本身就在这样的一种纵深喧哗当中就在这样一种争吵甚至对骂的当中然后才能体现出这个话题它的魅力和好玩的这个地方谢谢袁老师希望大家都是看看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对对对
对我们也会把这个书籍相关的一些信息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介绍里面给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也欢迎大家去选读这一套漫书文化序编里面其他的一些册子我也相信一定也可以得到一样的收获今天也非常感谢袁老师能抽出时间占用了这大半个下午对
很高兴又是跟大家认识其实这本书出来以后呢我也没有机会本来是想做一些现象的活动但是现在还没有机会展开所以这次我们线上的这个讨论算是关于这个小说的第一次比较我们也是听到了一些大家都读得很认真而且真的是对这个
话题感兴趣听到一些回馈所以感觉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一开始还是有一些疑虑说这样的书就刚才说的这样一种怀旧的方式的这样的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真的有人会感兴趣吗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播客愿意来找我来聊这个话题让我对这本书更有兴趣
我还希望这样的讨论以后能多一点就这种讨论比那种在网络上情绪的输出要有价值太多了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它其实有当下性但同时它又可以把很多的历史而且跟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也有大家都少少都跟这个热的某些东西都有这种观察或者是都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有意思这样来谈嗯
好那就感谢大家的安利给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袁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到时候等那个节目剪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效果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都很投入所以中间谈的比较多到时候看怎么来呈现比较好吧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都还是都可以保留没问题辛苦辛苦那就辛苦剪辑辛苦好
嗯好那大家下周再见下下周哈哈哈哈好那我走了一下啊然后再见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再见是谁出的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是谁出的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