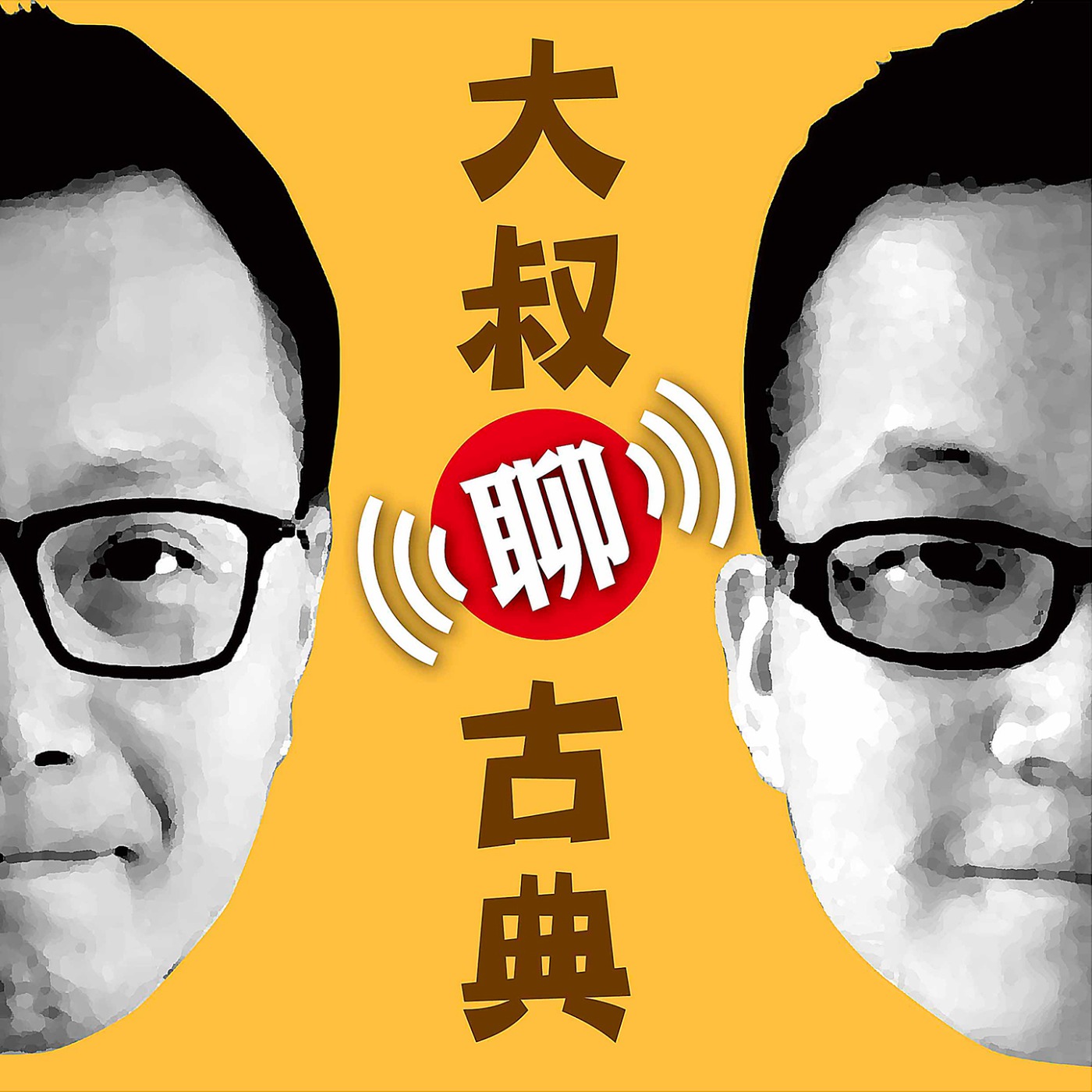
Deep Dive
Shownotes Transcript
歡迎收聽大樹聊古點 我是彭博我是余天音這次我們又邀請林天吉老師到現場了 歡迎老師歡迎老師這次邀請老師來上節目主要是上一次在錄節目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林天吉老師上次節目是在講小提琴的詩塵那時候你是跟林克昌學琴這樣子
我突然想到你指挥的这一块也有你自己独特的师承我直觉就想到很理梅泽然后
然後錄完節目之後我就想說問一下老師下次要不要來聊一下《橫逆梅澤》老師說 OK 那我們就來聊《橫逆梅澤》所以這一集歡迎老師到現場然後現在我們就先請吳宇婷先幫我們介紹一下因為我心一背的我覺得尤其是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愛樂者應該對《橫逆梅澤》沒什麼概念沒什麼概念所以
雖然我是 30 歲以上但是我對李美哲大師也是有點模糊的其實老實講我們 40 歲以下其實都挺模糊的因為大師走得早好像 2008 年 2002 年對 所以
但是我看了他的百有之後發現他是在台灣的音樂史上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等一下再請老師來跟我們介紹先請吳裕廷跟我們做一下老師的百有所以我也只能就網路上可以找到的資料所以我不確定就是待會再請林天角老師補充這樣子
那亨利梅澤大師他是 1918 年生於 Pittsburgh 一開始其實是那個 freetrainer 的學生 萊納因為萊納是 Pittsburgh 的指揮那他就是在出生在 Pittsburgh 然後接著他學完之後在兩個一個當地就是比較 local 的交響樂團叫做 Willing 交響樂團擔任指揮後來又到 Florida 擔任指揮
然後接著他就回到了 Peaceburg 交響樂團然後被任命為副指揮那這時候的總監是史坦伯格所以他就在這邊也是跟了第二個就是第二個大師學習然後他也常常就是有曾經為這個史坦伯格在卡內基音樂廳的演出代打這樣子
那就在那個代打的演出上引起了消題 蒐提的注意這位指揮劇播然後在蒐提的邀請之下呢然後 Major Joe 成為了芝加哥街場樂團的副指揮然後在這個位置上工作了 15 年
現在台北愛樂的影片當中提到他是民國 70 年第一次到台北 剋席 1981 嘛對 那時候應該是北市郊遊陳秋聖陳老師邀請他過來的然後後來再到高市郊後來就一些因緣際會然後就遷到高市郊那邊去所以在他擔任台北愛樂的指揮之前他其實來台灣好幾次了
嗯 有來過這樣子 等於在 90 年代他帶著台北愛樂到了很多歐洲啊 然後就是世界各地去巡演他是在 2002 年的時候在台北逝世享受 84 歲
這樣說起來林天啟老師也是萊納跟肖提的徒孫吧其實嚴格來講他的師承是 Fritz Reiner 剛有提到像 Wayne Steinberg 或者是 Sorti 其實他們是同事的關係雖然這兩個算是他的老闆當然現在我就很自豪講我的指揮的師承 Rainer 這一派下來
小麗芸 J 派我的話就是 AnescoJ 派下來的我其實先問一個問題因為在 BIO 裡面看下來我直接很當然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問的問題是他為什麼要來台灣就是在 1985 年他做了一個到台灣的決定說實在話二戰之後的古典音樂版圖
我可以理解指揮要去日本這件事情因為日本的古典音樂文化非常的興盛而且資料整理等等而且 NHK 就是 San Luis Obispo 等等其實已經非常有規模了然後卡拉洋整個都帶過去貝蒙這些國內史坦都定期去日本
所以如果有指挥去日本我可以理解但怎么会有指挥要来台湾发展而且一待就待了从 1985 一路待到也将近快 20 年的时间对但没有到就是说十几年的时间对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为什么下这个决定来台湾发展我觉得有可能是投缘对
就是说他来台湾课习几次的经验然后那个时候爱乐的 Lan Flat 团长跟于彬清于行政总监然后都开始跟他有接触所以那个时候苏南城苏市长就是说在高雄成立
高市交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透过赖团长牵线的状况去连到这些关系的这样子是对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上这样讲有可能会把老头就是我只是没辙在我们原来认为的这种形象可能会有一些颠覆这样对对要说破妹可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呃
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哈
梅澤當然他在所謂的第二線的一些交響樂團他有很不錯的成員但是到比如說我們講說到美國五大他也就是到芝加哥這個芝加哥副團這個副指揮這樣子但是他就是說以一個指揮來講總是會希望能夠再上一層但是目前他就是說他那個時候所面臨的狀況
说实在他常常跟我讲说他在芝加哥的工作的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不是那么理想那 Sortie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就是他是一个 Legend 还是一个传奇然后我们现在很多也都是听他录音长大的可是事实上那个时候他跟 Sortie 的关系不怎么样不是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有一点有点像是
帮 Sorti 解决一些他不想处理的音乐会的那种状况他说那个时候他在芝加哥就是因为他是副指挥嘛所以有时候这个音乐会他有 stand by 他常常就是可能是当天早上接到电话说今天 Sorti 他不指了你帮他上这样子他没有讲原因就是对就是你上你上对对对所以他好像在芝加哥那段工作的时间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一种神经很紧张对因为蛮高压力的吧
非常高壓力如果當天要指這個曲子如果我沒有指過或者是那我當天讀譜就天啊就是要花好多時間趕快 K 譜但是以就是說副指揮的這個狀況來講當然這些曲目他都有但是問題是他沒有跟樂團工作的時間啊
有可能就是一个追随热搜稍微比划一下然后就可能直接要演出就柳厅的工作对类似这样那几个重要的大厂应该来讲一定 sortie 他自己会他不会放过他不会放过这样子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好像就那时候台湾这边有 offer 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其实也跟他的夫人也有讨论过那我记得他的太太
是很支持他的 career 所以他说如果你觉得不开心然后你在台湾你觉得你有可能开心那你过来你就过来吧这样子所以好像也是在这样逐渐的接触之下然后他就最后就待在台湾这样好像也可以理解一个乐团要有两个国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
而且肖提真的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呼风唤雨的一个地位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去撼动他而且的确他跟芝加哥交响的确是
三四十年的合作我说肖体那种对啊那种很长期的这种都是他的那个而且这不仅是音乐上而且是政治上的就是你根本不可能去在这上面想要再获得一个比如说指挥的位置或等等所以如果想要真切的掌控一个乐团做出自己想要的音乐的确还是离开芝加哥是一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对那
那他在那邊因為看你是待了 15 年所以這個時間其實也蠻長的他也就是他不知道有沒有跟老師聊過他也是都要去別的地方嗎因為 15 年期間就是說他在芝加哥的收穫或者是說還是有一些他眷戀的地方嗎
这个部分就他跟我讲的其实没那么多不过听起来就是他那时候在芝加哥除了这些乐团的 routine 的工作以外他那时候也跟芝加哥那边的 Suzuki 小理型的那个协会好像也有一些往来然后有很多这种 school 到学校去推广的这些事其实基本上全部都是落到他上面去反正小提不想做就交给他做这样子
所以他基本上在芝加哥的狀況應該是非常的忙碌這樣子但是做基礎教育的部分就對了如果 Suzuki 那邊
所以他等於說在芝加哥那邊我現在側面了解起來他做的 Range 很大因為他那時候也負責很多現代音樂的發表跟演出這樣是喔對 他常常講說他拿到 John Cage 的上面簡直是一坨不知道什麼符號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樣子然後就也是硬解讀然後就跟著排練然後就是演出了這樣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因为有其实像现在乐团来讲有职权上其实有分得很清楚像后来我在 NSL 工作的时候第一个老板是林旺杰林老师他就跟我讲说他在他们科里夫兰的时候比如说有助理指挥那助理指挥下面有这种 Prentice 就学徒指挥然后助理指挥上面的话也有副指挥
associate 或者是 co-conductor 之类的那林旺杰老师就是在克里芬兰那时候他是 associate 副指挥那上面他那个时候老板是特园尼
对所以这个其实在制度上也有很清楚那时候在最早期就是说从廖年富老师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其实这些位阶也都理得非常清楚那个制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Round 到现在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我们都看不懂一直变来变去这样子 OK 好对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老头的状况其实就未接这个部分他们其实理理的蛮清楚是这样子对但是芝加哥那个时候呃
我觉得每一个音乐总监在 run 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使用他的副指挥或者是助理指挥 even 动用到这个指挥助理或学徒指挥这个位阶其实每个音乐总监可能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那美式的看法跟欧洲过来的这种传统的做法又会有点不同差别在哪里啊
其实也就是这一些卫生的定义跟职权每一个指挥的那种想法会不太一样这样子也会不会跟那个职位的那个在位那个人的个性就是比如说副指挥的个性如果比较强势或比较我想也会有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合约上面到底载明些什么东西这一定完全是按照合约的状况来执行的这样子对
剛剛老師有提到他在芝加哥指揮了很多現代曲目嘛那我還蠻好奇美哲大師他自己比較擅長的曲目是有哪個方向嗎就是說他是他當時到台灣然後帶台北愛樂還是以德奧作品為主嗎還是說他也帶了很多這些美國的作品來
其实都有其实都有因为我跟他他来台湾之后也弄过 Copeland 的很多作品然后我第一次参加爱乐拉的是贝多恩第四号交响曲那那个上半场是一个 Devil Shock 的小林音协奏曲好奇问那时候的协奏曲是谁在拉是邀请国外的音乐家来拉吗邀请国外那个时候爱乐的经营的方式应该是
就是跟两厅音乐园合作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两厅音乐园他们有那时候 NSO 没有出来他们那时候还是实验那时候还是实验实验所以但他们是住在就是住团在国家音乐厅的吗这个部分的历史我就没有那么清楚因为我进去工作的时候那个是 2000 年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已经是在音乐厅了
所以那时候在那之前的状况营运的那个情形其实我不一定是那么的清楚这样子那台北爱乐那时候对就是很理没辙会主动邀请一些国外的 soloist 来台湾演出就是在你的跟台北爱乐合作的经验当中原则上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要拿场地好像蛮困难的
据说好像是跟两天院有合作关系的话比较容易拿得到所以这个又是前面另外一段历史就是我们国家的对关于这个整个音乐文化其实从两天院怎么样去经营场地然后怎么样去策划音乐会或者是我民间团体自己去策划音乐会然后送神这些东西其实
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式跟制度我觉得开始有比较明确的制度跟模式应该都是 2000 年之后所以这个跟政府的改朝换代也有我觉得也有关系因为从原来的这种都是
我們小時候總覺得什麼都是關係關係這樣然後到開始覺得原來有法規然後我們大家要按照法規來辦事情那個思潮的改變其實蠻不一樣的那時候台北愛樂通常在哪裡演出啊也都是在音樂廳我印象裡音樂廳有然後在台北的話好像幾乎都是在音樂廳演出在台北的話所以在台北以外的地區
会在哪些地方呢因为就是现在台湾那么多场合但那时候应该很少那个时候高雄就是中正文化中心有了所以有在中正文化中心自得自善自得自善有在那边演过那那个时候是我专
专三还专四的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还是学生大概 1990 年的时候那第一次爱乐开始在国内办这样大的巡回这样子所以台南的那个文化中心现在是那个就文化中心对对对还是叫文化中心然后台中的港区是爱乐过去开幕演第一场那一场是演包英凯老师写的台湾音画 OK 对然后
中立艺术馆中立艺术馆他家旁边对那时候去弄了彼得与狼跟那个 Rabelle 的那个玩童经梦是所以那个儿童与魔法那么早就演过了对那个应该是爱乐在台湾首演的是对然后在更早以前好像有做过一次蝴蝶夫人的样子哇
然後因為是小的 orchestration 所以好像有某些部分是用簡單的好像是用合成器還是用鋼琴去彈這個是我進樂團之前的 1990 年代那時候其實台北跟高雄你不能稱之為一日生活圈就是那時候你來回跑來跑去
交通上之不便不方便对跟现在简直是两个世界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乐团这样子就是坐游览车然后下去六个钟头然后天哪所以一定是住在当地对那据老师所知一开始这个乐团的成员是如何招募的
然後那第二個因為是你說你是轉三的時候第一次去台北愛樂演出所以等於也像是因為當時還是學生所以是自己去報名然後 audition 給他聽還是說是怎麼樣老師介紹等等我其實如果在愛樂嚴格來講算是第二代的團員那第一代團員就是我們現在我們統稱為大佬的像什麼
蘇賢老人老師當然一定然後蘇政圖老師也在過李俊英老師那最近剛接任國台教團長的歐陽惠剛老師那中立前有楊瑞瑟老師那樹迪一定是陳偉霖老師然後長笛劉慧景老師都是大同寺這是我們現在目前在台灣教育界的
元老级的人物这样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被凑起来其实我不知道其实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一定就大家互相认识那早期于斌青于小姐她曾经在星象工作过一阵子所以有可能人脉是这样建立起来
因为像我小时候也是很常参加星象的活动像那时候只要他们邀请国外的音乐家来像姚仁罗桑啊这些人来的时候呃有大使班我是一定都会去参加所以有可能人脉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然后一旦建立起来是因为这些老师会在学校教嗯那所以他们自己去点学生就对了呃
可能就是邀请学生来 audition 那我自己本身是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社团的乐团是那个时候我们叫真善美观学院乐团那个这个社团哪个学校啊国立一专就
叫真善美管弦乐团国立专业校训叫真善美所以我们学生成立的这一个社团就是叫真善美管弦乐团那这个团呢是专门一开始就是专门演奏 pop music 哦
就是除了古典我们元素学的这种贝多芬·布朗普老才以外的这些东西我们学生就在社团玩这些东西有点像那个 Boston 的 Pup Orchestra 对对对基本上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那那个时候都是用学生指挥在带有点像社团一样对那那个时候的团长是
秦一李老师他现在是国台教对的巴颂首席对对对那他当团长的那一届他就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也有在爱乐锤了所以他会想说那其实我们可以把梅泽邀请过来课席一次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梅泽第一次见面其实就是在他来的那个排练上那个时候就是他排练是贝多芬第六号田园吧然后一次又走完我也吓了一跳原来我们可以一次走完然后在那个排练完之后他学长就很好心我们这有一个不错的学弟拉小学生你听一下这样所以他就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拉的 Vitali 的 Chaconne 整整十分钟他就听听完就说 OK 我邀请你来参加爱乐这样 OK 然后我就接到爱乐乐团经理那时候是黄永祥的电话黄老师的电话然后我就过来排练这样子
我其实想进一步问就是排练这件事情在台北爱乐排练应该说他们当时大概规划一年演出的场次有多少我还真不知道你参与的呢我参与的吼
好 后来我逐渐开始比较进入到乐团核心其实也不是说进到乐团核心就是因为那时候学生然后每次来参加爱乐都很开心都觉得我们都演得好棒这样很有成就感对一个学生来讲所以就三不五时很喜欢到爱乐去晃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像那时候欧冲阳 李哲义
歐陽慧如啊 我們這幾個就很常在愛樂就混在一起這樣子那混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黃永祥在辦公室嘛所以有時候就聊一聊 發覺 阿吉好像腦子對管弦樂團還蠻多 idea 的這樣所以後來那個時候愛樂曾經有一度一年是策劃十場音樂會
OK 时长我觉得在台湾以民间团来讲那已经是非常满的状况了对但是在时长音乐会的这种策划的频率的时候某一些职业乐团的毛病就开始出现了怎么说其实我指的就是人的冲突 OK 其实是这样这个事情我跟
前几天我来记者会就爱乐 40 周年记者会我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在 1990 几年的时候曾经有传出有某一个大企业要把爱乐整个买下来经营这样子对对对那但是后来这一个收购案就没成对然后我就我就那次我去跟老头上课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你不同意呢你不希望这样吗我说我们大家就
可以一起工作这样这样就跟他立美哲上课的时候问他对我问他对那大家都有固定薪水大家可以更专心的不用没有后顾之忧还没有后顾之忧不用跑外屋不用干嘛我们大家可以专心做音乐这样难道不好吗他就跟我说爱乐现在经营的方式他认为是最好的方式
我那时候听不懂就是我们现在这种 pick up 的方式固定 pick up 的方式 OK 就是说照理说 pick up 的话以经营角度来讲我可以每次都选择不一样的人可是爱乐的做法是都是固定的一群人那
那当然在爱乐的这个团运的名单里面有很多比如说首席那个时候除了苏老师以外还有林慧君还有其他我也曾经在这个首席圈里面算其中一个就是说如果苏老师林慧君老师他们不行的时候我也会担任到首席的位置这样子嘿
那当然其实其他的 principal 也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list 大家去论那每一次联络的时候可能最后组成名单会有一点点小变化可是基本上都是一群人对所以后来
我就比较了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我觉得他比较注重是乐团在排练的那个氛围他觉得必须大家是在一个很好的性质能够发挥最好的工作效率的状况之下来排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参加爱乐的时候觉得非常很不一样是说奇怪我们常常去练乐团练完之后像学校课常常上完之后哇
和期完爱乐的排练两个多小时完之后晚上还想继续跟人家嗨是在这边补血的对好像有点类似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就逐渐理解说他一旦有察觉到有任何 tiring 就是说团员可能有疲惫或者他自己有疲劳就是说他一发觉那个排练效率是不太在他的期待的时候他马上就叹停了所以
所以我们曾经有那种一般在台湾的这种排练都是以三小时来计算可是他从来不超过两个半小时
那常常也有出現的我們就來然後 Symphony 這樣走完一遍拜拜 see you tomorrow 這樣子這是美國指揮慣常很有效率的就是處理時間的方式感覺跟歐洲指揮比起來歐洲時間就是歐洲指揮就是多長就要多長就反正就練習一點但是美國指揮就時間到了就大家就該休息就休息了這樣
这个我没有正确答案因为如果你说有美国指挥或用欧洲指挥来分辨的话其实我想很爱恋的人我想到处都有这样子对那就是说很注重性节或怎么样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觉得应该是 sorting
因为他常常跟我讲他说有一次 Sorty 在练芝加哥然后阿尔卑斯教上去第一个排练早上的时候七八招这个也泡了然后什么都不对这样一堆泡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听起来已经快要可以演出了他说那个很 amazing 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那种效率这样子
所以他排练的风格是几乎不太用说的都是用笔画的嘛就是他可不可以请老师聊一聊他当时排练的风格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手上对他其实很讨厌停下来巴拉巴拉的讲哦
然后他常常觉得只会停下来巴拉巴拉讲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讲自己多伟大多怎么样他就是不选不要这样他说意思说你把团员凑起来这每一秒钟都在烧钱每一秒钟都在烧钱所以你做的任何事情它都必须要有意义它一定要有效果这样
所以你如果守团员比如说比下去守团员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你要停下来要来讲要解释的时候你每一个讲解实用的字句必须要准确这是我从他身上看到然后他也很强调你千万不要花时间在那边
讲一些是 full on 干嘛但如果这样子的话事前就要先准备吧就是说要不然不可能一上手就马上对就事前大概做些什么工作啊就是指挥或者是首席要先跟团员交代什么吗就是他跟我讲的是说就是说你的 preparation 就是你的准备的状况要背起来
背谱背谱对即使练乐团的曲子就是背谱对对协奏曲也是你就是要准备到能够背谱的状况你说只会背谱还是团员背谱只会对但是你演出排练你可以看 OK 然后他其实也有点反对上台是完全不带乐谱上去的他说你可以摆在上面但是你不翻嘿
心安的吗还是对他说那个有个心理因素的镇定的一个效果这样子啦对啊所以他觉得像他觉得阿巴都是很恐怖的家伙这样子
是 OK 能力强到很恐怖还是能力强到很恐怖这样他说他曾经那时候在 Sorti 在排马勒谷的时候那时候阿巴斗也在芝加哥然后到那个漫板乐阵阿达捷特的时候阿巴斗就走过来跟他说可以借我看一下总谱吗这样然后他拿去看据说大概看两三分钟谱就还给他说我背好了这样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吓一跳但是我现在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阿巴多早就全部都准备好都在脑子里面因为阿巴多的背谱也是非常有名什么复杂的东西几乎都是不看谱的这样写奏曲也背
我听说他跟小泽真儿两个是真的背谱背很凶的那种都不看谱的那种几乎都不看了卡拉雅也是其实到那个程度应该都不太需要看谱像伯恩斯坦我也不觉得他在看谱虽然他在翻谱但翻好玩的有时候就觉得看 DVD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
不知道到哪了他就一次给他翻个十页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其实他们早就背好了吧我发现上面只是一个经典的当然可能他们很熟可是他们还是可能一直指新的曲目或者说一些新的比较不熟的作品这还是很厉害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 YouTube 上面释放出来的东西很多了嘛像 Burn Stand 他那时候指挥春之记的那个还是黑白的影片也有他也是全部都背啊对所以
应该是这样讲啦我后来的体验就是说从老头跟我讲的这句话体验出来说如果你要想要乐团的排练是有效率的话好像这个功夫是不能省的
对因为很多东西是一旦你被到被捕被带脑子里面之后你脑袋瓜子会开始有些化学变化嗯你会从这些 patternpattern 这些嗯复杂的节拍或者是这种身部的变化里面你找到一个结构上你自己脑子理解出来的那种结构的方式啊
对那一旦你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你再放到乐团去排练的时候那整个乐团的排练速度就有可能变快所以那个时候爱乐的这种排练其实也被大家很诟病啊诟病对啊为什么那时候爱乐基本上老头的排练就四个排练上什么 Symphony 老才那个时候在 1980 90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状况能够演老才把它演好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
那时候马勒都还是觉得哇好不容易的事情这样那 2000 年之后像马勒 Stravinsky 这些就大家开始觉得这个好像对台湾的乐团也不是问题了这样子对那老师你再说这种排练方式在台湾是人家说其他人会觉得诟病诟病源是其他人的排练方式不是这样子吗应该是说为什么阿越排练那么少
对那个时候对我们学生来讲就普遍认为乐团其实是苦差事这样因为要不断的停下来重来停下来重来然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们在从小的乐团课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对那那
因素有很多啦那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同学之间可能这个同学不够努力或怎么样因为就是因为某一个人放炮某一个人落拍子然后我们就得再重来再重来这样子对那可是在爱乐或者是职业团这种层级来讲你一个乐手来参加的时候你本来就应该要把自己的部分就整理好了嘛那如果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来排的时候其实
的確是四個排練有可能做到一場音樂會就弄完這樣這個有個假設的就假設樂手自己本身是準備好了
假设乐手自己本身对这个 concerto 对这个 symphony 已经知道在里面有所有的音乐事件该怎么样被发生这样子是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其他的包含那个时候的职乐团可能都还有预设一些我们就是大家互相陪练的在舞台上陪练这样子在排练排练
舞台太恐怖了舞台太恐怖台練的時候陪練所以那個時候梅澤來台灣的時候他其實把一個新的這種
排练的这种文化带到台湾来那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就会变成说原来我们也能够做到这样的状况而不是那样子所以这个可能对以我那时候当学生的观念来看我觉得对整个台湾的音乐界有很大的一个大改变那来的还好是梅泽不是杰利比达克之类这种就是
哇那他不可能一整个就是他那个是超级超级爱练的超级多话的那种人那可以请老师分享两三个就是你印象当中在每次排练之下那种 magic moment 让你觉得哇他这个
這個點 或者是說他指的這個方式很讓你受到啟發哪些曲子 曾經在哪些曲子上有特別有讓你有特別的感覺其實我參加愛樂的第一場音樂會他有很棒的部分也有很糟糕的部分各自是什麼很棒的部分當然就是《被動人》第四號嘛那時候我記得是林慧君老師擔任首席這樣子我那時候坐在第一部小旅行
最後一個位置第八個這樣然後來那因為我第一次參加愛樂嘛那當然一定找點譜就拿刀看看裡面有些什麼就練一定是練好的才來這樣然後就排一開始就 Beyond Disso 我們從大學走一遍三十分鐘走完了 OK 好來 Contrad 走一遍好啦下班然後我想說這個聽起來還是有點亂亂的然後怎麼樣這樣然後第二個排練
就开始就比较多停下来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然后第三个排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可以上台了这样是然后那个时候两天要邀请的那个读奏家我记得是一个女
女性然后叫什么金塔我有点名字有点忘了她来拉德布扎克这样然后她来合的时候就在第三个章有一段就一直卡弹就一直她卡住她卡住过不去有一段那个黑米欧拉的那种比较复杂的那种二对三的牌子她就一直有点过不去这样子就好像合到双方都有点不太高兴然后在音乐会的时候就变成说嗯
梅泽从面向舞台的左边出场然后独家从右边出场有到这么不高兴我的天哪那个时候对我们这种小朋友来看神仙打架很专门的场面然后演出的时候就在台上我记得差不多快结底好像独座有拉到停下来然后从某一段他自己又接进来
而且我記得那個節奏好像卡的蠻緊的就是那個制度所以如果說沒有拔河它會很可怕天啊好精采那句小力情好有就是如果他自己本身的速率沒辦法控制的很穩的時候那我們樂團那種就很容易兩邊就錯開嘛對上半場就這樣然後下半場被人第四號就演的這樣
特別是第四月章我覺得好像在飆車一樣他把上半場不爽的氣全部都灌注在下半場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后来在几个就是说不管那时候要演财务德巴德九或其他的贝多芬或其他声控乐手就是每一次到某些地方比如说我那时候拉 Second Violin 会知道 Second Violin 这个时候可能要跟某一个乐器或跟某一个管乐器我们是同一个声部要 ensemble 不管是对位的管乐器或者同一个旋律线的总是在那之前就可以先感觉到
先感觉到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当我感觉到这件事情我抬头看见梅子他一定是盯着这几个部分所以这个就是他怎么有办法预先知道我们要干嘛这样子所以他背的很熟吗这些东西都很住在脑子里面我想应该是可是他从来没有背谱就是从来没有不带谱上去指挥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也后来就造成说我对被捕这件事情的理解一直在改变就是说那时候当他学生然后到后来自己出来指挥然后到现在这个状况就会对于这种被捕或对于这种捕应该弄到多熟的这种的理解就一直在不断的改变改变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说你原来是怎么想的后来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一直在变的内容是什么变的内容啊
我们就套一句那个时候 Mazel 来台湾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记者会好像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就是有关于排练他就说我们每一个指挥心里面要有一个乐团那你心里面有当你心里面已经有这个乐团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跟这个乐团排练你说心里面那个乐团排练对跟心里面这个乐团排练那跟真正的乐团工作的时候你只是把你心里面的声音
修正出来这样子所以意思说那是说如果你心里面对这个声音应该要形成什么样子有一个很清楚的见解的时候你实际跟乐团排的时候你的耳朵的运用你会马上知道说我心里面想要的声音是长这样那现实之间的这个乐团的声音它出现的是这样的声音那中间的差距多少那我要用什么样的
排练的语言我是透过手的调整就可以调整完这件事情呢或者是我需要一些很简短的字句去讲然后让乐团的团员可以理解然后马上就可以到所以那个时候我看 Mazeo 在排练那时候我就太神奇了这样
那时候拍展览会之后某一个部分这样他觉得不够好停下来我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谱上都有写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就是自己带那个纽约爱乐的功法过来给我们这样子这上面有写来再来一次那个比欧拉这个地方再怎么样声音对了下去所以等于说他如果发现一个要调整戏大概三次就解决掉了那
我那个时候有很明显的感觉到哇我跟这个人的那个差距太恐怖他这个东西他可能需要三次我可能需要十次或者十二次我才能够做到你说你心里面的声音你要把它放在真实的乐团上面的这个过程只要有一个
就有个地方需要改变你可能要一直花十次十二次跟那个真实的团员沟通对这是一个比率就是说我认为我那个时候的排练效率跟 Mazel 的那种排练效率是有这样的一个差距的是他有多太好了
當然像這種曲目他都已經比過幾百次搞不好都還破千次了所以那個經驗已經是太足夠了那時候我有聽我的前輩有講那時候他到日本去參加一個樂團然後
马赛尔好像在那个排练中间又去接了另外一个城市一个乐团的音乐会然后那个城市音乐团他就叫他的助理者先过去帮他练按照他的什么然后后来我一看演出当天
早上他还在跟那个那个现在工作乐团在排练那他怎么怎么过去演出所以后来发觉他其实早上排练完之后中午可能搭车还搭飞机过去然后就一个追随的时候比一比然后就演出了
另外那個樂團團員應該很緊張吧馬捷都一直沒出現這個人我也不知道怎麼是不是真的能夠全權代表馬捷就在那邊指這樣團員應該會很傻眼的想說我知道可是他那個時候來台灣的時候
排練次數也沒有很多然後而且這總排練次數前兩次還是我跟張嘉允老師那時候我們擔任 NNCO 的助理指揮我們幫他先走完曲子就是他的五個排練是兩套曲目一套半應該是一套半嚴格來講有重複的對所以我跟張老師就分了他的某些曲目先幫他把樂團走一遍然後他來樂團這樣排練這樣
所以真的会理解说如果当一个指挥他对曲子的结构了解到那么透彻的时候他的手的那个语言能够把这些细节全部传达出来说乐团整体的那种工作效率的确是可以
提高到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状况的这样子那你觉得梅泽在这上面他就是跟团员的传达就是团员的交流上面有一开始就很顺利嘛还是说其实因为毕竟语言不同或者是说文化不同还是会有一些需要磨合的过程吧
我进去爱乐的时候已经是根本不用磨合的状况所以我不知道那时候草创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像我进去参加的时候在爱乐里面它其实已经有形成某些工作的默契跟习惯所以像林卫军老师苏贤老师他们跟梅泽认识的都很早
所以他们大概已经相互之间都已经有一定的理解了下次再找苏贤大师对对他可能也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那可以请老师聊一聊就是你跟梅泽上个别课指挥的个别课的一些事情
当时他上课的模式他最在意的是什么或者说他对指导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如果以一个大方向来讲的话他比较像是哪一派的指挥或者是你觉得呢以一个大方向来讲这个真的是有一点他更像谁就是如果你要把他放在哪一种类型的指挥或者是有一个人可以对照我觉得老头的完整的形态应该是 Strauss
李察斯特勒斯对 OK 是喔斯特勒斯最近他的影带其实有都出来嘛在 YouTube 上面 YouTube 上然后有一个那个时候在慕尼黑格居然那时候 Sortie 在不是邀请他来指那个玫瑰骑士一小段的排练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排练斯特勒斯呈现出来那个样子应该是老头最想要的理想的方式哦
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在他的生命的晚期里面他非常推崇托斯卡尼尼是哦他非常喜欢托斯卡尼尼那个时候托斯卡尼尼那时候跟 NBC 友谊整套的这些影带也都出来他特别喜欢他指挥的那个贝多恩第九的
所以那个 LD 还是我帮他买的那买完之后他就一直把它贴在钢琴上面这样他的那个 Applied 平板钢琴上面平台他在音乐的比如说速度选择或者是他也是真的会比较倾向 Toscanini 那种很就是精神抖擞那种感觉还是
应该是说实在话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我不知道其实那时候台北爱乐的留下来的录音跟录影多吗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如果我们想要认识这位曾经在台湾耕耘很久的一个外国指挥对我们好像找不太到影像或是录音的资料可以去
YouTube 上有一些 YouTube 上有一些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在他的晚期的时候那时候公视刚成立嘛所以那时候公视其实有一系列的帮他就是说爱乐的一个现场的音乐会有拍成
轉播所以這些東西都有在然後應該愛樂這邊能夠上到 YouTube 好像都有放上去了 OK 對那那個時候愛樂的這些現場的唱片錄音的 CD 其實是有就是說有捐款給愛樂的可以拿得到這樣子他並沒有做對 沒有商業的販售這樣子原來是這樣子
对所以你要说他的风格其实有一点
因为我接触他就说那个时候 1990 刚参加爱乐然后到十年后他快要过世之前他的风格的变化非常非常大怎么说因为像我那时候刚去接触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演就以我们那时候演贝多芬或演那个 Chacoski 什么 Capitulo Italia 那些东西来讲他给我的那种感受是那种呃
非常有 energy 然后手一挥大概我们这些团员就身体那时候他应该六七十岁了吧将近对七十左右还是非常有活力非常有活力那时候排练绝对不做的他整个排练就是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半小时他一定就站在上面然后有时候常常一吼我们所有人整个就来了这样子可是到他后来
就是说去世前几年的那种状况呢又有点像我们比如说后来我们在看像查理毕达克的那种对于乐剧的这种长的这种 sustainable 或者是在内在结构的声音要去把它激发出来的这种状况又非常多他晚期的时候整个速度是偏慢的
对你觉得因为很多指挥的晚期速度也都偏慢对英巴不算很多人都偏慢你觉得因为我们理解是到底是指挥的意境到那个阶段还是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变快就是我会比较倾向于是身体的
的状况所以因为身体的限制多了所以自己在诠释上面可能要走入另外一个方向我现在其实觉得有点像是自然自然发生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整个人的成长一定有绝对的关系
那像比如说就我自己来讲在前几年都会觉得我的速度的使用有没有有没有合格比如说有没有完全按照作曲家的可是到这一年的时候我开始也会觉得说 OK 作曲家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参考可是我的身体比较倾向于喜欢什么样的速度
而且现在能够接受自己是能够慢下来以前是发觉自己有迟缓慢下来的时候会逼迫自己一定要快回来可是现在开始有觉得说这个缓慢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子
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跟生理跟心理一定有相对的关系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随着体能老化然后身体一定都是在不断的找新的方式能够去演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在我们几个小年轻人家就会看得很出来比如说像 David O. Strata 录的这个年轻的录的版本跟十年后
在录的版本那个速度就开始有差距然后包含音色的使用也不一样他早期的版本就非常拉的非常灵巧可是在后来的那个版本就变得厚重了许多那时候对于声音他就尽可能每个声音都是往比较饱满的方向去跑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比较有趣当老头开始走到这种风格的时候我们在乐团的团圆等于说
在默契的要求上就变了很多我们其实是这样讲就是说因为老头第一拍打到第二拍的中间的时间值变长了所以如果在第一拍跟第二拍中间有发生很多音乐事件的时候可能我们这几个首席就得互相去提醒对方或者是讯息的传递必须要足够
比如说在第一拍到第二拍有一个后半拍会有一个 16 分一幅在第三个点或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互相会去注意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照理说我们会觉得如果你要这么慢速是只会在这些比如说第三拍这个第三等份的拍子里面你是不是应该要提示些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是没有感觉到他有提示可是我们却可以在一起这样
那我们会觉得是我们的功劳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这样吗他在潜移莫花
有的时候就是说包含乐团之间这种默契的应用也是在指挥脑子的计算里面是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很奇妙所以就是他那种晚期的时候我们在演奏一些音乐的时候就拍子跟拍子之间感觉到的那种讯息的交流量就突然暴增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说最后面那几年出来的东西非常的感人然后我们很压迹呢我们有一个像这个查理威达克或像 Bernstein 这样的这种老成持重这种音乐性的这一个艺术家然后在台湾而我们跟他共度了最后这几年然后我们有被分享到这种音乐的
的奥妙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听一些比较老的录音你会听到那种好像拍子要飘移掉可是那个拍子飘移掉的时候你又听起来感觉哇好过瘾这样子
所以我們在台上其實一直在最後幾年都一直在享受這樣的一個過程這樣子那個是有一點奇妙這樣子所以其實橫提梅澤在來台灣的那個時候跟到過世之前那個時候在音樂上的轉變其實是挺大的轉變很大轉變非常大這樣然後
他如果以现在回想来看他那个时候最后一个阶段他应该是认为所有的声音都必须是漂亮的对他把声音那种需要的那种火气的这种东西全部都剥离掉这样子是对因为说我如果要做一个 spozando 那在音乐这内容里面他可能是比较粗鲁或比较残忍的东西那即使是面对这样一个
呃比较胆硬的内容的东西他也不希望真的把它做成那个样子那个声音还是必须要用一个很美的方式去发声这样子哦了解不过这个在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就是当他走到这个形象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要变成这样哦
对你的年纪应该在二三十那时候对在那时候二十几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可是问题是每次坐在乐团拉的时候看他手比下来我又不自觉的声音就开始所以那时候后面其实有一点矛盾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跟林徽均有聊到他觉得梅泽是个人精这样子人精人精就是他太了解人情世故是怎么一回事的
那这个影响我觉得一直影响到我现在这样就是说一开始我跟他是师徒的关系那你知道我们在传统东方的这种文化里面就是有这种一日为师终身回复这样子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逃脱出这种弗洛伊德讲的这种弑父的这个问题所以总是一旦你有能力了之后你一定会挑战
挑战这个就是说我们父子冲突也很多都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在我们传统东方的老师跟学生之间其实也很常发生这种事情
我以为老师都不能被挑战的所以还是很常常有时候学生挑战你跟着老师的缘分那个就掰了对所以其实我跟林克昌老师后面有经历到这个东西但是林克昌老师的处理方式比较东方的思维
所以其实我跟林老师有经过几年的转化到后面这个状况可是老头是他一发觉我开始要挑战他的这个状况之下他马上就很紧他就闪走了这样闪走的意思是闪走的意思是说他一瞬间他可以从师徒的那种权威式的相处方式突然变成朋友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可能真的美国人比较会在这种事情上就是
我朋友可能美国亲子关系本来就是比较就是父子可能也是比较接近朋友这样子因为东方人不可能这样子东方人我觉得不太可能可是问题是说如果你要让一个学生能够成长可以怎么样的话我觉得
这一个阶段的变化我觉得可能是蛮重要的对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就说包含我自己在教学对于学生常常都是一种否定的状况会比较多因为要修正因为要修正对但是有时候常常我们这种修正到过头会被修正到说其实学生有很好的 idea 你也把它给
念二杀了对其实我们到后来我们在交的时候常常都会有在考虑这样的事情这样子对可是这个我从梅泽身上看到就是说他一发觉这个关系好像不可以不需要在这样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就转变
抑或是他其实已经在等我长大等很久了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一旦他开始这个关系改变之后跟我讲的事情就开始娃把门这样开黄腔也开始会来了这样子我就是要问到可能是我最后一个问题他私底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很利美者甚至因为你从 1990 年跟他开始接触到最后的阶段当然我不知道贴表情但就是我很想知道这个指挥在私底下你们怎么跟他接触他在台湾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他在台湾的生活状况我想应该是很开心因为我们这些音乐家都是朋友然后三不五时固定都会去找他
然后已经都是吃吃喝喝了那台湾住在哪里啊住在哪个区域他那时候住在新海路那边的一个顶楼的一个小阁楼然后那个小阁楼也布置的很好它有一个小花园这样子然后那时候
也让他养了两只猫一公一母这样子然后他一直都在讲说你看哦那只公猫后来因为发情就把它拿去咔嚓掉了之后结果那母猫就当场当天回来就是那个就离家出走了因为那公猫 no ball 就开始讲这些对讲这些对然后他那个阁楼也好像弄了一个泡水池这样子
泡水池不是泡澡像游泳池那样小小的这样所以夏天很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来来我们来泡水池不台湾人的生活方式不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常常也是电话来
就是说 Paul 你今天有没有空我说有啊那时候因为我在空军总部当兵嘛所以离他那边很近那走路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到我今天中午想吃披萨你会不会来陪我我说好就过去了这样所以其实没有这么严格或者说这么有距离的这个师徒模式嘛这样听起来其实
一开始是很师徒啦但是后来的那个状况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样但是因为我跟他的年龄差距其实太大因为他在我心里面总是是一个大英雄这样子然后年纪应该是都快要当爷爷年纪对他是他是我爷爷的那种那种年纪这样子对所以哇所以
听起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的生活这么的随性的就是说这么不是随性的就是 casual 就是没有这么的严肃没有那么严肃他唯一严肃只有在排练跟上课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也有一次在那边上课不知道比哪一个原物曲还是什么就比一比我开始在那边摇屁股这样他一脚就踹过来他说 don't dance 哈哈哈哈
所以在台灣你覺得他在台灣最重要的音樂會是或是說你印象最深的一場音樂會是什麼就是你參與過的我想應該是柴舞吧柴舞柴歌是個第五在國家音樂廳的在國家音樂廳的柴舞那個是第一次愛樂就是說進到某一個規模然後他就帶著大家開始嘗試柴舞這樣子
那那个时候我一直很喜欢 Burns 但后来晚期跟这个女儿爱玉露的那一张因为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很迟暮的至少在我那个时候学校刚出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完成体的财务这样那后来当我们知道也有上财必达克那种的也是很棒这样可是在那场财务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经历了那样的一个
過程那麼的緩慢然後每一個音色每個慢慢的唱然後在第二樂章說集體高潮這樣子對然後當然我跟他寫這《La Haciaturia》那個可能對我來講是一個沒有辦法不忘記的一件事情這樣子怎麼說音樂裡面創造了些什麼
沒有那個音樂的事情是一件事情可是那就是說以我一個學生就是說他的學徒的這樣一個孩子然後當我小藝情有一定的程度所以那個時候他願意有機會然後我們一起弄這個 Hatchaturan 的小藝學徒對我來講那是很大的一個光榮這樣子
对那从老师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梅泽就是带给台湾哪些新的启发也好或者说他带给台湾音乐圈的什么样的事情是你觉得很珍贵的我可能骄傲的一点讲如果没有他来台湾的话可能后面林旺杰 简文斌他们的路子会很难走我觉得他来台湾之后一方面当然如果说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他把一种新的排练文化
带进台湾来了然后因为这种排练文化的改变所以也促使那时候公家乐团他们必须要对自己的体制跟经营的方式要做出改变因为那个压力其实很大因为那个时候爱乐经营的状况几乎是把公立乐团打得死死的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就像比如说像世交现在有了英巴尔这一个对啊那就世交整个声势就带上来那一方面当然也是讲说英巴尔本身他经历的很够经验足够所以他看过太多的事情那时候对 1980 年那个年代的台湾来讲
当然我们前面有肖之有包克多有这些国外来的艺术家但是在梅泽来台湾然后他带着爱乐其实等于是第一个对于这种职业圈的生态他树立一个新的方式我不要说标准新的模式原来职业的乐团的工作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
所以后面的比如说不管 NSO 或者是 TSO 或者我们就国内的职业团一旦是这样就是说原来可以这样工作那为什么我们团做不到
那当然自然而然他就会开始反思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透过一些组织改造啊或什么东西去优化让自己能够更好这样所以这一个火花其实我认为是从梅泽来台湾之后他逐渐影响影响出来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
因為後來老頭在 2002 年走了那時候剛好 2000 年的時候剛好也是九龍兵開始接 NSO 的總監那前面三年有林旺傑老師也在
在 NSO 工作这样所以其实现在的职业团的现在目前的这个荣景其实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展现出来的对那当然对职业团或者是对我们公立系统来讲也会有问题因为他们都要上咨询台的
執訊台執訊市交要被市議會執訊那個時候因為也是拿教育部的經費所以立委他們當然有職權可以去關注這件事情所以變成說以國家或以公立的資源在做這些事情他們非得做出這些成績來愛越那個時候
就是没有这种没有在公立的系统里面虽然也是美联有拿那个时候文件会的补助这样可是艾域可以做到太多的事情了他可以到国外去巡远那时候美加这些地方去待过然后这样那无形之中我相信对于公立乐团来讲一定产生压力是个威胁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用用市块一点投资报酬率的东西来看 CP 值很高 CP 值很高啊 2 月 5 一年花你国家多少钱而且绝大多数很多资源都是民间的这些企业团体赞助出来那你国家一年吃这么多的经费然后你们才做出这样的成绩像话嘛
这个可以说进去这个我没有问题因为两个系统我都待过所以我想这样的评论我觉得是可以说出来的当然 2000 年之后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根据那个点走到现在的这个样子那是后面的新的故事了对对对
今天就是謝謝老師來我們現在我覺得不僅聊亨利梅澤而且是聊了老師你在在台北愛樂那段時間的我覺得所見所聞吧你看到了這個台灣古典音樂環境的變化特別是樂團的方向尤其是樂團的方向這些真的感覺聽老師講古很
很超快希望老師有空再來我們節目一起再聊別的主題這樣 OK 那今天我們就到這邊謝謝老師掰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