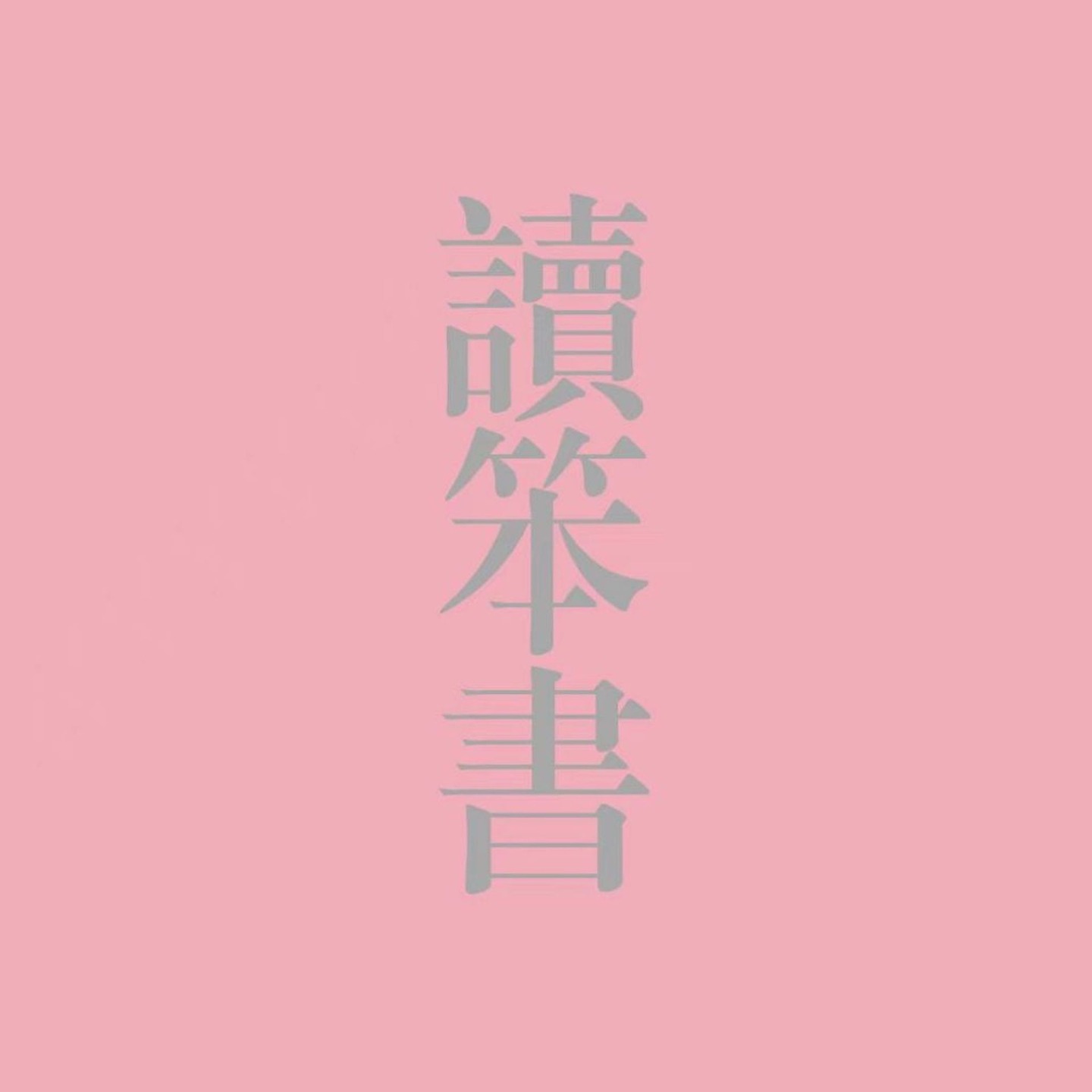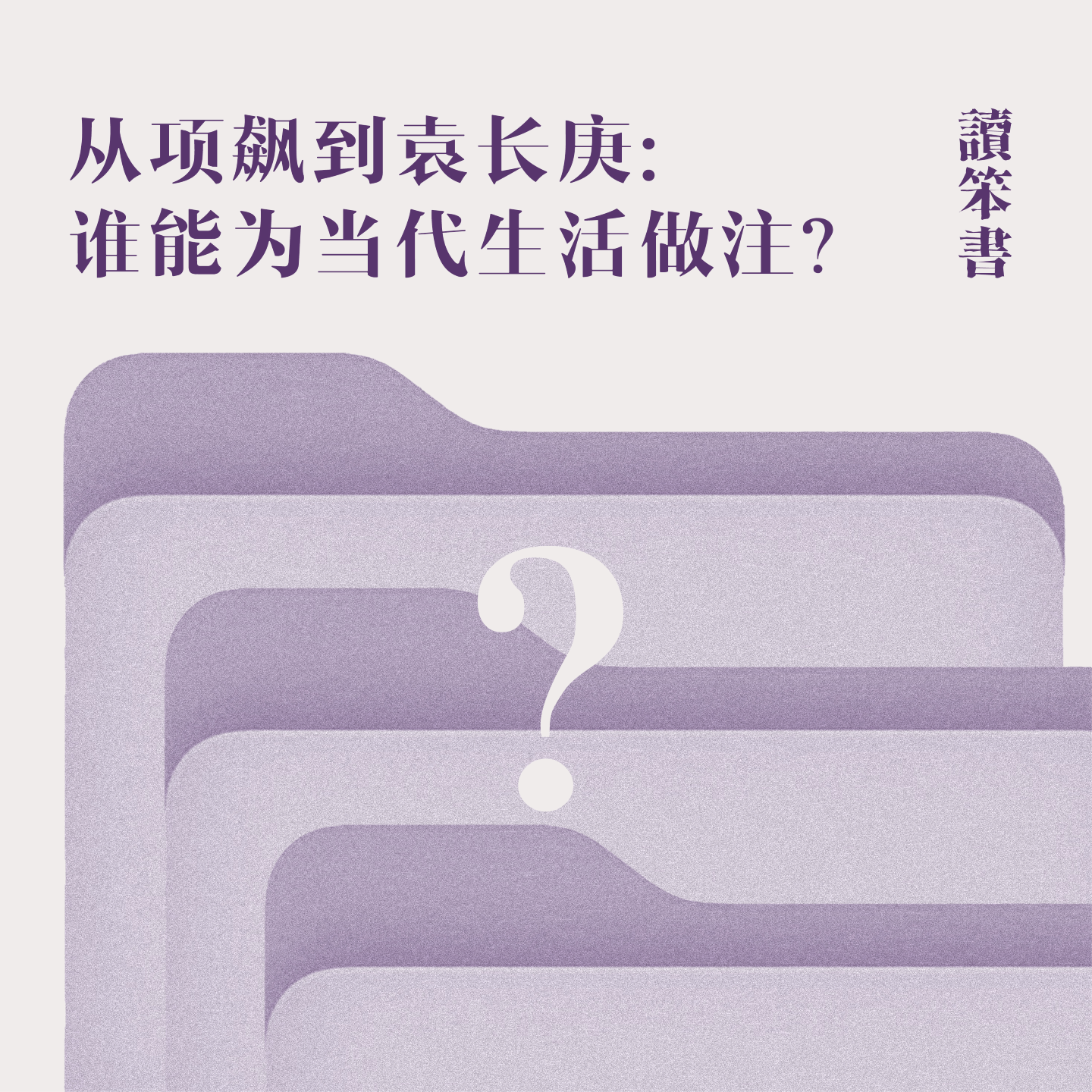
Deep Dive
Shownotes Transcript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读本书的三月节目我是主播郭细雨我是主播鸭老师这一期节目是我和鸭老师在几周前想做的一个选题因为今年我自己的身份从学生转到找工作的年轻人然后鸭老师的大学老师身份也在经历一些学校内部的变化
然后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或者产生一些困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我们讨论的话题中总是离不开袁长庚橡标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发现从去年 24 年开始袁长庚似乎就打引号代替橡标出现在各种平台上为年轻人打一解惑
这里代替打引号是因为更准确的说法我们觉得应该是链接就是它不是一种高位对低位的理解而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达成的某种共识然后在这种共识中袁长庚为这些当代年轻人答疑解惑于是我们就很好奇从袁长庚的走红到项标的逐渐的冷却也是打引号的冷却背后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社会变化
我们想要试图通过这期节目梳理一下我们事业范围内的大陆学者的出圈史然后我们想要问的也是究竟谁能为当代生活做主然后在正式开启本期节目之前我们还有几个点想要说明第一个就是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把所有出圈的学者给囊括进来所以我们选择的学者都是我们两个人目之所及
极的出圈的一些学者以及这些学者可能是我们平时关注比较多的学者而第二点的话是一些学者严格来讲他们可能并不算是学者他们可能是创作者大学教授但是我们还是把他们算了进来因为学者也仅仅只是一种身份吧
然后第三个点是这个出圈的时间点我们把它严格划定在了 2019 年以后因为再往前就无法确定了而 19 年的疫情它算是对所有人的生活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我们开始关注学者包括
包括橡标上 131 提出附近的概念其实也就是在 2019 年然后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先对这五年来的出圈学者做一个大概的梳理以下的梳理我们是按照学科来分类的然后第一个学科的话是人类学这个部分由鸭老师来进行一个梳理那关于人类学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
很进入大众视线的学者第一个就是 2019 年通过参加十三一然后提出父亲概念之后进入公众视野的向彪老师那这几年向彪老师他陆续出版了比如说把自己作为方法那在那本书里面向彪老师就进一步去拓展了他相生的这个概念以及如何通过构建父亲解决年轻人面临的一些
困惑或者是问题然后最近几年上方老师他有另外一个研究的主题就是如何构造年轻人的生命力以及如何面对共同焦虑那袁长庚老师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从 2024 年开始他
他也是逐渐走入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部分的视野当中那袁老师他本身的研究领域其实应该是医学人类学包括生死教育等等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因为他在讨论年轻人的时候他是以主动走进的姿态进入年轻人的世界所以他慢慢的成为了互联网上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觉得那个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学者
然后第二个要讲的学科的话我们就想讨论一下社会学因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确就是我们刚才讲从 2019 年之后是大众视野范围内非常显学的而且被大众觊觎了很多光环的一些学科那如果谈到社会学的话我们认为就沈亦肥老师他应该是属于非常活跃而且很出圈的学者之一那沈亦肥老师他本身是复旦大学社会系研究社会性别亲密关系及家庭亲子关系等等
我们这里主要想讲一下沈亦菲老师走红的一个契机就很有趣的是他是在 2018 年然后 B 站上有一个大学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脱单这么难?社会学系视野下的热恋与冷静那这个很明显这个标题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个是 2018 年的时候才会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当时也是整个社会性别还没有完全被建构出来然后大家也在试着摊开讨论亲密关系
但是放到现在的这个语境当中我们就会觉得现在就是情绪是非常抽象亲密关系的问题可能从本质上就不存在也有很多人觉得亲密关系已经不再需要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么就可以斩断或者说我个人就可以选择隐身独处
所以这个是沈亿伟老师的走红如果是放到现在而言的话其实他还是否能这么出圈这是我们在做这个梳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疑问但是沈老师他是所有刚才或者是我们接下来会提到这些学者之中
少数的在各个平台都保持更新频率比如说抖音比如说扫红书比如说 B 站比如说微博尤其是他的短视频的播放量依然是保持到现在都会有几十万的播放量因为他本人身上就是有各种复杂的标签比如说他是妻子他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也是一个女性的社会学家
所以沈老师他可以把他自己作为过来人的各种的成功经验复制粘贴到他的受众当中所以现在在看沈老师的话就会觉得他比较像是书店里一些摆在中央的畅销书的逻辑就满篇都告诉你说
有什么样的人际交往指南,亲密关系的修复指南然后会告诉你要避零一些类区很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他今年在 B 站上更新的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名字叫做当代年轻人的脱单指南但我看到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这个年轻人指的是谁呢?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课程人介绍写的是 B 站年轻人最新人的爱情教授我觉得爱情教授这四个字好像
可能更适用于他走红的 2018 年或疫情之前但是放到现在爱情教授这四个字他的针对的对象又是谁需要这样的爱情教授呢就他需要的受众群体又是谁呢然后这个课程的介绍写的是说解答新时代的爱情新问题但是我翻了一下就是沈老师这个课程他所要解决的新时代的爱情新问题比如说女性下架该不该辞职回老家找对象爱情里有没有真命天子等等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 10 年前会讨论的一个问题而放到现在这些问题可能都已经用放弃的姿态而抵消了这个问题本身所以通过在复盘沈亿肥老师的我就会发现说我更加认识到了就社会性别它的基本盘到底是什么样的受众和群体
就我们可能以为一些已经揉碎了讲烂了的问题或者说就异性恋或浪漫这个桌子我们都已经下桌离场了当然会发现其实下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人还是在那张桌子上讨论说这个饭怎么可以做得更好吃怎么可以粘贴复制一些可以用的经验嗯
所以我就想说那这些人他可能就是或沈亿伟老师他所针对的一些大众或受众可能就是如果一些事件发生在舆论场上这个舆论场的风向到底是怎么样应该就是由所谓的这群基本盘的受众来决定的这是在整理沈亿伟老师的时候会觉得和现在很不一样的一些语境的问题那
然后接下来就是法律这个学科法律这个学科我选了两个老师一个是罗翔一个是劳东彦老师先来说一下罗翔老师然后罗翔老师他其实一开始走红就是在 B 站因为关注他的人也知道他最开始火就是源于他在一个法律的考试辅导机构叫后大法考讲课时的一个一系列的视频当时有人搬运把他的这个视频搬运到 B 站后他就火了
我看的有一篇文章分析说其实推动罗翔快速出圈的可能是他讲课视频中大量奇葩狗血然后又耸人听闻的犯罪案例如果来梳理他走红的时间线的话我是以他在 B 站发出的第一条视频为起点
然后这个时间就是 2020 年的 3 月 9 日这个视频如果现在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他的那个视频里面提到希望同学们可以培养法治精神成为法治之光然后也表示他日后会在这个平台对社会热点知识进行分析还会分享一些他读书的个人感悟我觉得看这个视频很有趣的一点是他在视频里喊话的那个对象是同学们因为他在 b 站这个
平台上发这条视频的嘛所以他的这个对象就非常明确的一个同学们的对象这个也会对应到我们下一部分聊就是不同媒介在这个学者的出圈过程当中充当了什么作用接下来的另一位也是近几年比较出圈的法律学者就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劳动彦老师
我来看劳动院老师进入大众视野的时间线的话其实他最早是在 2019 年的 1 月份他当时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劳燕东飞但是后来他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发了很多跟时政有关系的一些文章然后这个文章也是多次被删除然后之后他又在 2022 年 2 月份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叫直面真实的世界发了之后就被封号在这之后他又开设了微博如果大家关注劳动院的微博的话会发现他在近几年其实有很多涉及滥用公权力的议题上他都是很猛烈的参与的
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拐卖妇女案还有去年公安部和网信办推行的一个非强制性的网络实名认证就是向中国网民签发网号和网证核验实名身份仪式的它都是有很热烈的一个参与的
去年下半年劳动院老师也第一次参与了播客《罗斯在临景》的录制那期播客我看现在的收听量也破了 10 万然后也是这个《罗斯在临景》这个播客过程过往当中最受欢迎的一期节目之一然后为了这期播客我又去翻了一下劳动院老师的微博他的微博的话目前的可见范围是到了 2023 年的 4 月份然后在那之前的微博是无法可见的
然后这个就是法律的这个学科大概的一个梳理然后接下来是哲学的梳理哲学的话就是我们俩有一个分工我这边就主要是想梳理一下刘晴老师因为我本人是看过她的一些课程或者说她之前的一些书籍刘晴老师的话她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他长在学在以及他的自我发展的高峰期可能都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这样一个学者所以他探讨的比较多就比如说像自我呀他人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共生关系他探讨了很多的包括说年轻人现在普遍弥漫的虚无主义的共同情绪要怎么解决以及个人价值如何体现自我选择然后包括一些文科通识教育的普及
像刘琴老师之前有在得到 APP 上开设过一些课程比如说像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然后我觉得刘晴老师她现在书里看来她针对的对象其实比较有限我觉得她所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那种想以哲学当作一种方法就恢复自身本身就有的一些人文精神是真的所谓爱智慧的那样的一群人然后也想从价值啊智识啊自身的逻辑和生活趣味等各方面都过上良好生活
培养可以进入公共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种人但是现在再来看的话就我们待会会讲尤其和向远长庚老师所针对的一些受众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些人对自身的要求包括他对公共生活的畅想想象和他对自己公民身份的认知而言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对这个就是我对刘晴老师的疏离那我要说的就是也是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很受欢迎的网红哲学学者就是韩炳哲提到韩炳哲很有意思的是我是按照中信出版他那一套书的时间来算因为严格来说的话在 2019 年中信一口气出版了他九本书之前国内是有出版过他的书的只是在那之前其实都没有什么火花
然后以及我自己又回顾了一下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他的我就想到我可能应该最早就是从一些播客里面听到韩炳哲这个人就是如果大家去看韩炳哲的走红的历程的话我会觉得他的出圈其实是离不开中文播客的一些推波助澜的当然这只是我作为读者非常个人的一个观察然后在我搜索他是如何在
中国走红的过程中时我也意外发现了其实关于韩炳哲这套书的责编胡明峰他当时其实因为出版韩炳哲所经历了一些一波三者的历程吧就是起初韩炳哲这套书他其实并不被营销看好的
他的起因数也不高在对哲学书的营销上可能这些营销编辑可能也会有一些拒绝就打引号拒绝的思维就认为哲学书可能读者都读不太懂然后最早读的人也确实不多这个编辑甚至因为销量不佳最后辞职离开了中信但是在离开的这段日子里面这个韩炳哲的书就逐渐开始被人看到
然后编辑也提到其中一件事带动了更多人关注韩炳哲就是 2022 年 9 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勤在 B 站推荐了《爱欲之死》这个视频点击量突破百万以及我看了一下韩炳哲在多半上看过的人的标记数排前三的三本书
我读出来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排在第一名的是《倦怠社会》豆瓣上有 2.1 万人标记读过第二名是《爱玉之死》它在豆瓣上是有 1.7 万人读过累计短评也有 6000 多百条第三名是《他者的消失》也是将近有 1 万多人读过的回到我自己的一个小观察我个人会觉得波克对韩品哲的书也是
起到了一定的推广作用的原因是比如说我经常听一些播客就能听到主播引用韩品哲我觉得首先是因为韩品哲他关心的议题比如说像他者的消亡啊什么新自由主义公济社会这些话题本身就是播客常会出现的一些选题
其次的话韩炳哲的书他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必备读物但是就是你去看小宇宙 2020 年他们给的一个用户画像当时的平台超 75%的用户都是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及海外的且都是硕士级以上的学历占到了这个分布的 40%人均收入在 14800 多元以上这个画像其实也是能比较对应到韩炳哲的这个书所面对的这个读者群体的
然后接下来的另外一位哲学学者就是陈嘉应我觉得陈嘉应可能跟其他几位的风格有一点不同的是因为陈嘉应老师其实他在 19 年之前也就是在我们划定的这个时间起点之前他就本身就有一定的知名度
然后我觉得他和另外几位还比较不同的是他的走红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媒介在推动的你也很难去找到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或者是因为某件事情某个困惑他就走红了但我觉得大概还是能梳理出几个时间点的
那这里不得不提到就是我们在梳理过程中发现的就是推动这些学者走红的一个节目就是十三一李佳音她上的是十三一的第一季也就是 2016 年当时她就上的那一集节目就她有一些话也是比较出圈的
然后第二个时间点也是我自己个人就是画的一个时间点画画的时间点就到了疫情的时候我首先我得声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内部的一个视角就是我记得疫情期间微博博主用户公书他在微博上发布过一段陈嘉印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的摘抄当时那段摘抄因为特别切中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于是在微博上那条微博是被很多人转载了的
但是我觉得陈嘉颖她可能在我肉眼范围内我觉得她出圈的两个时间点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文学的部分文学这个部分呢也是有我自己一个私心在的因为这两位学者他可能首先他不像前面几位那样出圈而且依然是但是依然是属于在参与公共讨论上很热情的人然后另外就是他们都是文学类的学者或者是正在大学教授文学相关的老师我觉得我把他们算进来的时候还是比较
忐忑的因为文学这个专业也是我跟压老师这次在聊到的就是你说他小众吧他其实又长期在人们的视野范围内但他又不像社会学人类学这么边缘但你说他主流呢文学在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又不是那么的重要我这个部分画进来的两位老师是张一威和张秋子
张一威的话如果大家关注他的话他一直都是非常活跃在各个平台的然后也是长期做各种内容分享的学者创作者大学老师他自己的身份是很多重的比如说他会在知乎上回答问题也会在杂志上写文学专栏几年的文学播客里面其实也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像他和鲁豫录制的那一期言中花束也是有 25 万的收听量另外一位的话是张秋子
其实其实我最早知道他应该是在一些非虚构报道的公众号就是看到这些公众号会去写他的文学课当然我觉得他肯定不算是那种很出圈的学者甚至他的定位严格来讲也不算是学者更像是老师但是我想把张秋子老师放到这里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在 202
22 年出版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像唐继科德的眼镜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对文本的一些解读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就是今天的文学学者在回应时代的一个方式这也会在接下来我们会聊到就是为什么文学学者是比较难以出圈的为什么在一个动乱或者充满各种不确定的时代人们会更倾向于把问题抛给人类学学者或者是社会学学者而不是文学学者然后
然后最后一部分是心理学学科这个部分由亚老师来梳理心理学学科的话我们也是主要围绕两位心理咨询师一位是崔庆龙老师崔老师的话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聚焦当代字体心理学和依恋心理学方向然后主要研究的比如说像母婴互动还有临床心理治疗之间的理论和实践关系
其实崔老师他 2021 年之前他其实在知乎上是有非常活跃的然后提供了非常多高赞关于心理学的关于依恋心理学问题的回答但是其实崔庆龙老师他主要的走红是在微博上而且崔庆龙老师和其他刚才我们提到的学者很不一样的是之前很多学者或多或少的都有参与过一些传统媒介方式比如说像
电视或者说像最新的比如像播客这种以声音为媒介的这样一种传播形式但是崔晋龙老师他最主要和大众见面的方式就是文字他几乎很少参与播客的录制也几乎很少参与比如说综艺或电视节目的录制所以说他和大众的沟通的渠道好像就只有文字然后我就在梳理的时候我发现说他这个唯一的和大众交流的尤其是在微博上以文字的方式和大家交流其实
非常符合他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我觉得总结而言就是他所解决的大众现在的问题就是低能量人士如何通过修复日常来获得情绪能量
就他很常在微博上解答的一种状态就是当代人为什么我们会能量很低这种能量可能包括情绪能量为什么会一直看起来呆在原地动也不动但是其实我觉得崔庆龙主要给大家一个回答就是他就告诉你说你呆在原地不代表我们没有前进过没有后退过不代表没有做出任何行动他可能就是我们也前进过也后退过但是最终你好像看起来是你的相对位置没有变
所以我觉得它很像我在看我们之前都很喜欢的一个韩剧叫我的解放日志包括我觉得它的走红和当时我的解放日志的走红也有一定的相似的心理背景就是它都在讲说如果我们都处于一种情绪很空的状态你也没有特别悲伤但你也没有特别值得为之开心和嚎叫的精神状态的时候我该怎么解读我现在这个看似很低能量的状态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给的非常多的情绪的描述或者说解法的描述就好像说我们所有人都在一个管道里面然后你在一个管道里面你来来回回你也出不去虽然没有走出这个管道但有的时候你敲一敲这个管道他如果传出一些回声然后在他看来那就是一个叙事的回应
然后另外一个心理学上就是大家若言可见非常受到关注的就是李松卫老师那李松卫老师其实他出圈的时间和沈亿北老师很像而且他们两个路径也很相似都是说当亲密关系可以被
通过各种公共议题或者说不同的媒介比如说像综艺恋综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拆解细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像一些心理咨询师比如说李松蔚老师他常常站在关系当中的弱势的一方来去回应和解答一些问题包括给
像一些职场关系当中的比较弱势的一方比如说像下级像打工人他常常站在这种弱势的一方来去解答你这个情感困惑也是说告诉你很多的问题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或者说你处于这个弱势但并不代表你要以这个弱者的思维去看这段关系
所以他比较肉眼可见的就是他参加了非常多的相对的这种综艺来去剖析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李松蔚老师和崔庆龙老师他们两个虽然都是心理学方面的咨询师但是他们面对大众的媒介和形式也是截然不同的好第一部分呢我们先是做了一个大概的梳理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进入到一些具体的现象
那第一个想聊的就是我们在之前梳理的时候就提到的为什么我们觉得文学学者很难成为那个为当代生活答疑解惑的角色我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就是几年前在听不可理论的一期播客那期播客的嘉宾呢是戏剧从业者胡玄奕和何琦
他们两个人就是硕士是在台大读戏剧系他们就说在那期播客里面他们就提到他们当时有一门课是小说家童韦格在教授然后有天上课的时候就在上课的过程中吧然后外面就突然下起了雨童韦格就说刚刚雨水在屋檐上发起了一场政变
就是我当时听这期播客对这个细节印象非常之深就是会觉得好像学文学的人他对万事万物是有一个自己的审美在的所以他对很多事情的解释也是有他自己的审美在的听着其实真的挺美的而且挺台湾的但我就很好奇他们当时听这个话的时候就有什么具体的感受或反应吗他们播客里面有讲吗
播客里面他们没有就是具体讲但是就是当时胡轩一提到这段话的时候他有学那个童韦格讲这句话的那个语调就是反正就是台湾人的那种语调你大概能想象吗就什么刚刚雨水在屋檐上发起了一场政变就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我觉得对他们两个人可能他们对这个细节也是非常
之深的对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挺美的而且他的受众也是这样讲的很有审美趣味的所以他才能过这么多年他还能记得这句话当时老师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调或语气就我也想到张秋思老师在他之前的一个采访里面举了一个他学生的例子因为记者就问他说你觉得文学对于一些非重点学校
或者毕业以后他也不会用文字来作为职业的学生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张秋泽老师就说他有一个学生中文系毕业之后就在游乐场做兼职然后有一天他去上班之前游乐场下了雨那个游乐场的椅子上就积了很多雨水嘛他一不小心就一屁股坐了上去然后裤子上沾的全都是雨水
其实如果放在生活经验里面来讲的话你在上班之前遇到这种事情你肯定是很想骂人的但那个学生他突然之间他就动用了一个文学的念头他觉得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而言的话其实这个瞬间是非常生动有趣还有点天真的
所以文学它真的非常需要一个人他有这个审美的能力然后我们需要动用我们全部的审美能力而且有的时候你要用一种可能是局外人的角度抽离出来吧但同时你对生活要全情的投入你可能才能获得那一瞬间的解放但那个解放就你说它意味着什么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闪进来了然后留下了一会儿但是很快又飞走了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那个例子就让我觉得文学还是很有意义的就起码这句话这个语调那个雨水发生一场政变就这句话我还会记得十年二十年但它能解决什么吗好像也不能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解放了或者是被改变了吧
我觉得你说要审美这个要求本身也是挺高的那我的第二个例子其实是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就是我曾经在几年前当时我在备考然后我当时就
偶然读到张一威在一篇采访里面的一句话他就说我们对爱要有兴趣才能走得远其实这句话你这么一听就是他是非常抽象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是对实实在在的我正处在背考中的我有很大很大的鼓励那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到底指的是有什么具体的语境吗
他这句话就是来自一篇关于张艺薇的专访吗我当时觉得他那个语境就是张艺薇因为他自己就这么多连写了这么多的小说采访者就会想问他就支撑他写这么多小说背后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因为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他那个话的语境也不是说你要去爱一个具体的人啊或者具体的一件事情啊我甚至觉得就是
它有点像是一种信念因为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其实靠的是恨在支撑因为恨是很具体的吗你恨某个人恨某种恨某个事情和某个不公平的比如说以什么政策之类的那个恨是很具体的但是你会觉得那个不长久真的能长久下去做一件事一定是有爱的所以要有这个信念我觉得这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文学的思维也很
相似就是文学的思维他就不是告诉你答案因为告诉答案本身就是有点反文学的然后文学的思维就是会需要你去强调你自己的主观性强调你需要审美然后他本身也不解决问题但他会把这个问题给研化给柔化
但社会学和人类学好像就是他们会拆解问题分析问题但是我觉得文学的不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一种解决吧下面就我来简短的聊一下就是也是我在这期播客里面有一点想聊的就为什么法律学者出圈会面临诸多的风险
因为我就发现法律学者出圈的风险几乎是所有学科里面学者出圈风险最大的因为我之前就在思考为什么拿罗翔和劳动业老师来说他们两个人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刑法学者而刑法的特点就是刑法它是属于公法然后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司法
然后罗翔老师他在《权力的边界》这本书里面他也写过对刑法的一个理解他就说基于国家和个人地位的天然不平等所以公法的基本要义是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又要对国家这种秩序的维护力量进行必要的约束因此对个体权力的尊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公法学者看待问题的基本视角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当这些功法学者用这个基本视角在社交平台上去解释一些问题时其实就天然具有某种风险我觉得这点在劳动院老师身上是特别明显的那罗翔可能还和他走红的路径有关系
因为他走红的地方是在 B 站嘛而 B 站本身他是一个造梗的地方加上他在 B 站发布的内容很多时候就是他的身份有一层也是内容创作者的身份罗商老师在 B 站发布的内容很多时候也跳出了他自己的专业领域我读到一篇文章就说其实对内容创作者来讲你跳出专业领域的行为是十分冒险的
那篇文章就说一来是观众的兴趣度从播放量来看的话罗翔主页中读书感悟道德哲学或是偏生活类的视频相比法律类是要大打折扣的二来是互联网上人们对高知群体犯错的容忍率也是相对较低的对公众人物来说表达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主要由鸭老师来负责因为鸭老师和袁长根的身份其实都是大学老师并且你们面对的学生群体其实是比较相似的一群人嘛然后这个部分呢就着重由鸭老师来讲
好然后在聊第三部分之前就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日常的工作实践当中会不自觉的使用一些学者的方法论的一些瞬间或者是例子因为我的学生其实就刚才讲的和袁老师的学生的群体非常相似就大部分的学生来上这个课他们只是肉体出现但灵魂并不会出现他们对这个课程或知识本身也没有什么探究的欲望然后当时就是我和学生在对一个泛文化里的话题进行探讨
但就发现学生对这个话题根本没有什么感受或想法但我当下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说我知道大家现在可能电视剧电影看的都不是很多书读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说至少我们还可以亲身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然后我说完这个话之后我自己都有点一愣因为我觉得我下意识脱口而出的居然是没关系
因为放在以前我可能就会振臂高呼非常痛心疾首的呐喊说同学们为什么呀这为什么不能多读读书呢这么多优秀的电影电视剧艺术作品为什么不能看看呢我觉得这里想要
就是因为刚刚本来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因为你说你的学生读书读的不是特别多其实可能跟这个学生群体还是有有一点关系对对因为我以前就会特别傲慢的问说为什么大家会对于书籍影视作品艺术生活没有任何的兴趣但后来发现就是其实我们的学生包括跟袁老师的学生很像的就是
大家虽然坐在同一个教室但是你不能忽略他们背后的家庭环境或者是阶级光谱我觉得你要要求一个人天生的对比如说我们讲的文学有审美能力或者对生活有情趣还是挺傲慢的一个要求因为我觉得我上学期认识你的时候你跟我讲就是你对你学生的状态就还是有点那种痛心疾首的感觉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读书为什么不看剧或者为什么不走进剧场看一些脱口秀
哦然后就当时我说完这些话之后包括我说没关系之后有一个女生她就突然就笑了嗯她她那个笑什么意思就那个笑其实蛮妙的但她肯定不是嘲笑的意思嗯
就这个笑应该就是学生他自己承认说他对这个世界既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然后也缺乏热情而且他也发现老师也承认这一点也发现了这一点但老师对这一点就是他既不震惊也不苛责也没有冷嘲热讽所以当时这个学生就他就笑了他可能觉得是说我们作为师生我们一起很坦然的接受了这个事实
然后他在这种很善意的老师的确认当中他也得到了一点解脱吧我觉得而且我自己说完没关系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脱就还是挺微妙的因为我想象那个场景的话就你必须得跟你的学生同时在场你们共处同一个空间共享同一个语境你才能理解或者你才能读懂他的那个笑是什么意思他不是通过文字就是可以说明的
对因为那个非常微妙因为作为老师其实你最怕的就是在课堂上学生无意识地发笑所以当下他笑的时候我其实是有花 0.1 秒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说他是不是在嘲笑我但我很快就否认我自己说不是这绝对不是嘲笑
因为我觉得就在那个瞬间我说没关系的时候我是那个主动张口而且我是那个主动说没关系的人所以我就有一种信心就是这个笑绝对不是对我或者对我们师生关系的一种否认嗯
所以就这也在让我想,袁老师为什么会成为现在年轻人,尤其大学生,甚至是具体而言像我的学生这样的大学生,他们会非常信赖,而且想要交付自己的沮丧这样的一个学者或者是公共人物。我们接下来就想尝试着分析一下袁成庚老师的三种面向,然后第一种面向我们给他总结的是一个在生态体系中的学者。
因为袁老师自己在一个播客当中也提到过他觉得东北人应该是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就因为他们首先打破了中国人对于故土或者说对某片土地的执念然后而且东北人他不断地换地方比如说迁徙到海南但他们都能很快速地和卓北的人群打成一片形成一个很小的关系生态系统
就按袁老师的话说他觉得东北人跟谁都能当亲戚吗当然这个亲戚他指的肯定不是基于血缘关系发生的亲缘关系他其实指的就是说你不管走到哪你都能跟别人成为一种小型的有机互动体
所以袁老师他自己你比如说他从深圳这种很崇尚精英效率的地方慢慢迁到了云南这种地方然后云南他本来就是一个生态体系更多样的地方而且也是人类学的重镇嘛所以我觉得他自己都是实践了这种小型的生态体系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梳理过第一次知道远长庚是什么时候大概就是他 2022 年他跟也是
也是人类学者安梦竹就他们是一对夫妻嘛他们上了随机播动的朋友再见系列的第一期节目然后那期播客的录制节点就刚好是袁长庚准备从深圳搬到云南也就是他即将在云南大学任职嘛对我们当时还说就对他搬书那个印象对特别深对
就所以相应的我觉得因为袁老师他自己经历过很多这种迁徙或迁移包括他自己是山东人然后在香港读书然后又去深圳教书然后又转向云南所以他从深圳转到云南的时候他平时所接触的学生也就从一些精英学生或者说对通识教育或人文教育更推崇的学生或者是能够主动发问的学生然后就变成了现在在云南大学这种非精英的对
对学术或者说对生活都更加沉默的学生群体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袁老师和其他学者的区别就比较重要因为他不像其他学者其他学者像我们了解的向彪老师他们可能就是凭借自己的学术成果出圈但袁老师他其实就是凭借他的课堂这种范围更小但是和学生互动更加有机或更加稳固的这种生态体系而走进大众的而且他自己从教授一群精英学生到
我们暂且把它称普通学生吧只是在学生这个分类的话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也是能促使他更在现场的因为精英学生毕竟是少数嘛且相对来说这群学生他在阶级上也会更处于中产这个时候他对大学生这个群体的观察和体悟
就是他到了云南之后他的对大学生群体的观察和体悟其实是一件更自然的事情因为对于我如果我是带入学生的身份来讲的话我也会觉得我听到他讲的那些话他对大学生的体察我会觉得更有说服力那第二点我们就觉得袁老师他呈现出的一种面向就是一个拒绝呐喊的施者尤其是在面对很沉默的大众的时候
这点我们想通过他和向彪老师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分析因为向老师之前提出过附近的概念很多人都知道但这个附近我们觉得应该是重建附近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曾经有过附近但因为一些原因他们变得更加的原子化
但这些人他们求生意志很强烈所以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很多人会给向老师写信这些信可能长达几千字甚至是几万字他们非常渴望从向老师那里得到一些回应的方法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小红书上也没推过是吧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会给向老师写而向老师真的会回复但是我觉得能够书写邮件的人其实本身就是求生意志非常强而且求生能力也很强的人这些人可能就具备之前我们所提到的他就有文学的审美能力而且他会想办法拓宽自己对于生命的一切的理解能力然后去进行自救而且我们之前还聊过其实写信或者写邮件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训练的对是其实门槛挺高的对
而且我也能想象就能给向彪写信的这群人他还是很有生命力的一群人对因为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可能我不一定是那个真的有勇气去写出这封求救信件的人我在小语中就听了一个 00 后的女生她分别和向彪老师还有袁长庚老师进行过对谈很明显的是她在和向老师对谈的时候她整个人就呈现出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特点她非常有求生意志有非常强的求生能力有很强的审美能力
然后她当时在跟向老师的对话里面因为向老师她自己人不在国内嘛所以她对国内年轻人她一直都是非常有好奇心但一直都是一种观察和请教的位置所以向老师在整个谈话过程当中会经常问到这个女生一句话就是哎那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要找向老师去求救的话首先我们需要自己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嗯
我们当时讨论到这点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这个跟项标和袁长庚他们所处的位置还是很有关系的就可能我们今天聊的会有点混乱就是聊着聊着会突然发现学者的这个身份本身就挺混乱的就是从你讲的这点就能看出来项标其实他占的位置还是一个学者的位置而袁长庚他占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
就跟鸭老师本人的位置其实有点像就是也是一个大学老师的位置只是他可能自己有他一个学术背景在对有的时候会觉得上标的位置很像做访谈和研究的位置对因为本来也是这个社会学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嘛
对我最开始就觉得他俩一个就是当我们喊袁老师的时候这个老师可能指的就是一种职业和身份但我们喊向老师的时候可能这个老师指的就是向彪本人在学术界的一个权威和地位然后就袁老师很不相同的是他自己说他自己面对的很多学生或所谓的大众都是一种欠缺生活经验也缺乏对生活的热情
那我理解为就是可能就没有力气去像跟向彪老师求助的那种群体一样他们没有力气去写一封长达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邮件他也没有什么生命热情去构建自己的附近那这些人他可能很难展开自救所以我自己的工作体验和观察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学校的确是这样
由于就是日益高中化的高校管理其实很多学生他哪怕是在同一个宿舍他们也都不知道对方的证件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证件但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写邮件能写几千字或几万字的邮件的人能对自己进行自我梳理的人他一定是有自己证件的人这些人可能都去找项标老师去了我们这里有必要定义一下证件就因为证件这个词它其实就不是我们这里大学校园语境下的词
我觉得可能就是是不是这里的证件更多是指我们我们要不要去对公共事件展开展开一个讨论就像之前压老师提过的一个例子就是你问你的学生有没有去看再见明天然后你的学生跟你讲说他是
嗯他可能是还是有点想去看的是吧但他没有人可以一起去看因为我是我是会觉得可能一起去电影院这件事情或者是看这种有明显的女权意识的电影就是一种政见的暴露那我理解的就是可能他们对这种暴露是会有恐惧的因而也会
显得更加的冷淡会吗会因为那天就是我跟大家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你们最近有看还有明天吗然后就很沉默我说其实是我说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和朋友一起去看的电影我说那你们会有想和哪个朋友去看吗他们就摇头不知道我就比较诧异我想说那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说我身边哪个人是安全的是和我站在同一政见立场的去可以看同一部电影的人
所以我当然就觉得说学生他们真的很需要一个站在高位的人当然这个高位是打引号的就需要这样的一些人很正式的把一些议题或公众话题摆到这个台面上来然后非常公开非常郑重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对他们很重要他们是很关心的他们可以和谁去看这样一些有证件的电影但他们是不会和周围的人讨论的
所以他们对这些议题哪怕你提的时候他们的回复和反应往往也只有沉默或者最多的时候你能看到几个学生的眼眸它是亮的被点亮了但袁老师做的就是他不会把一些人的反应比如说沉默理解为麻木或者没有反应袁老师他就会走进这些人的沉默然后接受出这些沉默而且告诉这些年轻人说你的情绪其实是对的那第三个点我们想讨论的就是
当然也是可能最有争议的一个点我们觉得袁老师呈现的最后一个形象就是很符合时宜的反叛者形象因为袁老师整个人首先我们先讲他的语言体系就有一些对体制的反叛比如说我看过袁老师的一篇学术论文一般而言学术论文其实是已经比较剥离了个人的写作特征的但袁老师在论文里面会把某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称为企图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
袁老师在非常有限的语言表述的体制范围内还是最大限度的呈现了他的一点反叛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说的是袁老师个人社交头像的展现就如果大家去看过袁老师的小红书或者是他的豆瓣或者是他在云南大学官网上简介的头像会发现袁老呃袁老师很常呈现的一个形象就是穿着一个 T 恤啊
然后头是侧面的 45 度仰望天空的一个视角有的时候会敲个二郎腿然后穿一个工装裤再穿一个马丁靴整个人看着就有点摇滚也有点反叛但是呢你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符合社畜的形象就他应该也会在工作群回复收到的那种人
所以就觉得袁老师这个形象包括在他跟他妻子之间的关系的表述当中他也会透露出他对父权制的一些反叛但这一点很妙的是他常常是作为一个山东男人呈现出爱妻形象但我当时就是我对这一点就我们俩讨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表示怀疑的
就是这也是袁长庚我们觉得他很打引号聪明的地方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王感很强的人而且我们冲的浪还是同一片浪就像鸭老师之前还用了一个形容词你说他像客服是吧对就他知道说什么话是正确的
就他不仅知道他说什么话是正确的而且知道怎么说是正确的比如他上随机播动那一期节目我印象就很深他就一直在提他老婆人类学者阿孟竺就对他的一个无论是从性别上还是从很多公共事件上的一个再教育包括他到西西福高速那一期他还在强调这一点这个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很政治正确的人但是我当然不是在这里说这个政治正确有问题而是我在讨论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今天是一个女性学者她在播客里总是提到自己丈夫对她有多好的话如果她提了很多次我在想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女性学者百分之百会被骂吧
当然其实你说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有一个很对应的女性学者的形象了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对他呈现出的这种非常符合时宜的反叛者形象需要提出我们的疑问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结论一定是质疑或不质疑而是我们觉得提出这种疑问本身也很必要嗯
这个前期我们聊的时候还在半开玩笑就是半严肃的说其实这里面的每个学者的长相也是很不一样的在这里不提具体的名字但我们当时就说其实某位男学者的脸就给人一种很复杂的感觉看着很正人君子但是正人君子这个词的意思好像就是你在公共环境里面呈现出这种形象但是你私底下好像就不知道了
对就无奖竞猜大家可以自己听到这里猜一下说的是谁反正我们也没有答案但是如果一个男性他呈现出的就是非常正人君子的形象我们到底应该是全盘相信他还是反而要有所提防呢同样的我们又是发出一个疑问但是也是觉得这个疑问是很必要的嗯
好那这一部分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想聊一聊学者出圈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在场但是聊到现在呢我们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表达者的在场那我和鸭老师在这一部分可能各自站的角度会有点不同我是从一个接受信息的角度然后鸭老师呢会从给出信息的角度来谈一谈
就是我和亚老师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场可能放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科不同位置下其实都有不同的定义的比如以我个人为例的话我去年在英国读研的感受就是其实在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你甚至只需要走出你的房间你走到街道上你加入到一个队伍里那就已经构成一种在场了
就是某种程度上我对厂的理解就是一个地方的公共生活是否存在且活跃的理解这个公共生活可能要在这里做一点狭隘理解因为我生活在川嶼嘛其实你说
穿越人一起吃饭喝酒打牌是不是公共生活这肯定也是一种公共生活但他可能和我自己想要的公共生活比较不同的是我想要的那种公共生活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人携带不同的想法然后我们都拥有不同的思维但是今天为了一个议题聚集到这里我们来进行思维之间的一个碰撞或者是达成某种高度的理解的这个碰撞对我的
日后的行动是要造成一定的影响的但是一起吃饭这件事情其实它对我日后的行动和生活是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因为吃饭就是吃饭嘛所以我觉得我在思考这个在场的时候我觉得它没法对所有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比如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做移民研究的学者那你在国外的环境里面其实你是可以和国外的移民进行对话的这个就是一个在场但如果我今天是研究东南亚移民的学者但我人在重庆那我肯定没法说我算是一种
打引号的在场吧就是因为当然我相信就学者他总是有他自己的办法可以去构成某种在场的但是这个场如何搭建他可能确实是需要我去付出一些努力的所以我们在关注橡标和圆长庚甚至在这一部分我把何为也算进来就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其实都是关心非常相同的群体的就当下的中国年轻人嘛但是如果你用嗯
在场的标准去看他们三个人的话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圆肠羹是很受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欢迎的因为它就属于在这个场里面而橡标呢至少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它在德国生活然后它又是通过邮件来与年轻人进行交流这样的在场方式好像始终对我至少对于我来讲我从一个获取信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难以信服的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里讨论的语境就是当一个学者他要介入当下的中国社会那这个在场就会作为我信任他的一个标准之一那我的角度可能就会不一样一点首先我想就做一个对比因为以前的学者我觉得他们提供的在场主要是经验的在场比如说一些书本经验的在场或他们自身经验的在场我觉得尤其以一些
哲学的男性的学者会比较明显那这些学者他们常用的一些词就比如说叫召唤或者是重建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尤其是我从我的工作经验当中观察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面对的受众他不读书或者说他对生活既没有特别大的热情也没有根据生活经验形成特别多的常识他更没有建立附近的生命力
那这样的在场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情绪的在场因为这个情绪就意味着非常多非语言的交流比如说如果公众不提问就像我的学我的学生们他们就是不提问那沉默那这种沉默学者需要如何解读需要怎么回答因为很多非语言的变化
就很多非语言的表达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共读一些情绪比如说我们要共同去理解这个沉默意味着什么以及如果我们发言之后那这些受众或者学生或者大众他们还是继续保持沉默闭口不答或者这种拒绝的姿态又意味着什么你可能就不能把它理解为叫麻木或者是没有反应
所以我作为一名老师的话我会希望我的学生可以能够被今天的学者或者是公共话语场所接住吧这是我做完整期节目就最大的一个感受我会觉得说我把一些公共场域开始慢慢转手转给我的学生们那对我们这些学生或者年轻人而言就今天暴露自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暴露过后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或关系不一定是可靠或者有趣的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我的学生或大众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就有一些发声者或者说一些学者可以走近他们然后可以低下头看一看他们的境遇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在场首先意味着学者要自我暴露他们需要意识到说即使自己是发声者他可能需要更针对性的把自己暴露在对应的受众群体之中因为就今年的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我当时需要给学生就选择话题和讨论的一些资料我当时是有做一个暴露自己的选择的我思考了很久说我觉得我今天要不要讲妇女节的内容但是如果我选择这个话题就意味着我会丢失掉一些学生但是我后来就做了这个选择我觉得有些人或有些学生他在妇女节这一天他应该得到英勇的安慰所以我当时就在进行资料呈现的时候
我就做了我的选择然后我知道我的学生有一些他们可能对女性主义不感兴趣甚至是有点反感他可能会对我选取的这个内容选择忽略但是当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些学生抬了头眼睛有点忽闪忽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暴露自己也是很值得的
课后就有学生很开心的跟我聊他说之前也有老师讲过其他类似的话题当然是男老师但完全是不同的角度他从没想过同样的材料居然还有今天我带给他这个角度我当时听完之后我也很感动我就跟他讲我说对啊我说所以你们需要去识别说即使是老师即使是学者即使是一个发声者他们都是在按照自己的立场和偏见呈现出给你们想看到的内容
好然后第四个部分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会从我们个人的生命经验出发来聊一下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学者的因为最后这个部分是我私心特别想聊的想到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问鸭老师就问他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密切关注学者的动态的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我要很认真的去梳理这个时间线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节点就是疫情
虽然疫情前我也会读一些学者的采访啊书啊什么的但是我真的意识到我需要读一些在某个学科类的专业学者的观点的时候大概就是疫情因为那时候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其实是非常
杂乱无章的并且你会自动区分哪些信息是来自于官方哪些信息来自于自媒体哪些信息又来自于传统媒体哪些信息又来自于你信任的人就是我觉得所有人在那个时候都在经历一种对信息的重新认识
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最信任的信息来源其实就是一些我信任的人而这些人他们与我的关系就有点像是学者与他们渴望交流的对象的关系我们必须是真诚的我们必须是有一定共识的然后我们必须是共处在同一个语境的如果这些都达不到的话我就很难信任这个信息的真实度和真诚度
这也回到我们之前聊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学者的在场很重要就拿我自己举例子的话我会想到我在英国读硕士这一年有一两次我在街头上参加巴以游行的时候就有一瞬间我会想到如果此刻我人在伦敦如果大卫格雷伯还活着很有可能我们会在街头相遇我觉得这种在场就是我判断一个学者他的学术能力是否达标的一个
一个指标之一然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也非常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就我不想要只是坐在学院里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我是希望我的研究最终是要回到街头的回到附近的
这也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吧就是这几年可能我对权威处在一种屈昧的状态就是哪怕我很喜欢一个学者他发表的母片论文但是我也不会对这个人有更多的崇拜也好喜欢也好就是我对任何人都还是有怀疑在的
以及就是我也像我们之前聊到的说我们都知道橡标他已经开通了一个邮箱的链接那我们要不要给橡标发邮件呢我就觉得我是不会的因为首先我不会预设我的问题会通过和香标的一来一回得到解答
其实我也不觉得我的问题他能给我解答还有一点是我跟亚老师聊到的就是在我这里我觉得今天橡标他作为男学者的这个性别的身份已经远大于他的学者的身份了我不会在一个性别为男的学者面前百分之百暴露我自己那我也想问亚老师就如果你你会不会给橡标发邮件呢
其实问题我想了之后我觉得我也不会就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聊过说向彪老师之前有在一个议题那个议题是关于说他觉得
高中生早恋其实是对于他反抗这个体制的一种方法对他觉得是对个体的一种松动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说这其实作为一个男性的角度而言的因为其实你在高中生里面的爱恋很多时候就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文理科呀或者说那女生对天然对一种学理工科的成绩好的男生的崇拜等等他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非个人因素的但是我们当时就觉得像老师这个观点其实
可能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年代也不一样然后性别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他的这种所谓的学术观点跟我们而言就不是那么的在场至少在的不是同一个场嘛但是我也不会跟他去写长达几千字或几万字的一个邮件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如果你要给一个人写几千到几万字的邮件去剖析你自己的话你必须得对这个人全然的信任我觉得我很难做到像你刚才所讲我需要考虑到他的
八九十年代就是高速个人发展的年代和我现在所经历的年代以及他的性别和我的性别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能有这个心力去写几千或几万字的话我觉得我把这个文字写完之后我自己已经得到了情绪上的某种出口和释放我可能就不太再需要说另外一个和我在不完全在同一个场的人给我一些解法了就是我们说写邮件其实本身是有一个很高的标准的
对而且就你文字写很多之后你会觉得可能那个问题本身它也已经失真了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这期播客的一个原因吧就我不知道鸭老师在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因为这期播客做的过程其实还挺困难的然后每当碰到一个难点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我做这期播客的初衷是什么
包括促使我想到这个选题的起点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它是我过去五年生活的一个注解不仅是学者在为当代生活做注解也是当代生活在为我们个人生活做注解因为我相信这些学者之所以能被选出来一方面是有他们的主动性在的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我们大众的选择就是为什么是他们这背后反映了什么是我做这期播客的一个初衷吧
然后我就在做这些播客的梳理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啊原来其实我关注一些学者是因为我一直想对一些公共话题或者公共场域一直保持一个参与吧其实我们最早开始就我们那个年代最早开始是有非常多的公共媒体可以
可以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就是带领我们所谓这些学生或大众对公共话题进行一些讨论的那个时候我所认为的学者不一定是某个具体的人他有可能是一些报刊一些纸媒一些媒体人比如说像南方周末呀新闻调查甚至枪枪三人行吧我觉得都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就带领我去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并且可能形塑我对于一个真正的理想公民是什么样子的一方面的塑造但是
就是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后来这种公共环境就逐渐消失了我所能接收到的信息和一些舆论场的能量也消失了因为在那个
就是大家可以对公共议题有所发生的年代的时候就你会觉得是有人在带领着你往前走的我们是可以对时代进行一些振臂高呼的然后我们个体也是被时代寄予厚望的你是可以去改变时代或者甚至时代是可以等你的那个人但后来这些环境都消失了之后其实我本人还是没有放弃去寻找就是我想怎么参与这个公共生活以及我还是想成为一个良好公民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理想出了一系列节目包括八分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像梁文道啊陈丹青甚至包括马世芳就是对我各方面在音乐美术绘画甚至徐奔的一些相关的课程都还在告诉我说我还是有能量可以去自我寻找我如何成为我想成为那个理想公民的样子但又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也累了我也没有什么能量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像我在金银岚的小说就你的夏天还好吗那篇同名小说里面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人已经不在场了但是我特别想有一个学者或者有一个公共人物或一个公共事件来去发现我这种不在场去关心我的离场去找到我去告诉我说你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把你给看见你可以被看见
所以后来我觉得让我实现了这个被看见且再次能够以听众或主动和被动的形式重返到这个舆论公共场就是播客因为通过播客我觉得我的一种沉默或者说我的一种呼应也形成了整个舆论场的参与我也被赋予了某种权利很多的话题它也可以得到一个深度的探讨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那个
参与的沉默的但是也可以成为很有力量的一段但到现在如果再问我对学者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的话其实我会更愿意把学者当为一种职业因为我现在就自己也有一些工作经验之后我会特别喜欢那样的学者就是
他特别热爱自己的这个职业但他也会很憎恶这个职业他可以非常的熟练利用这个职业但也会被这个职业所利用他会得到一些但是他也会觉得有一些东西他不应该得到或者不应该失去就很像我们看完那个初步举证的时候跟你分享那种心情我就很喜欢初步举证里面那个律师甚至是写初步举证的这个编剧就你对你的职业
你爱他你也恨他你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甚至是一种会被很边缘很在夹缝里面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它特别的真实然后也能特别的连接到所有的人在场的或不在场的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