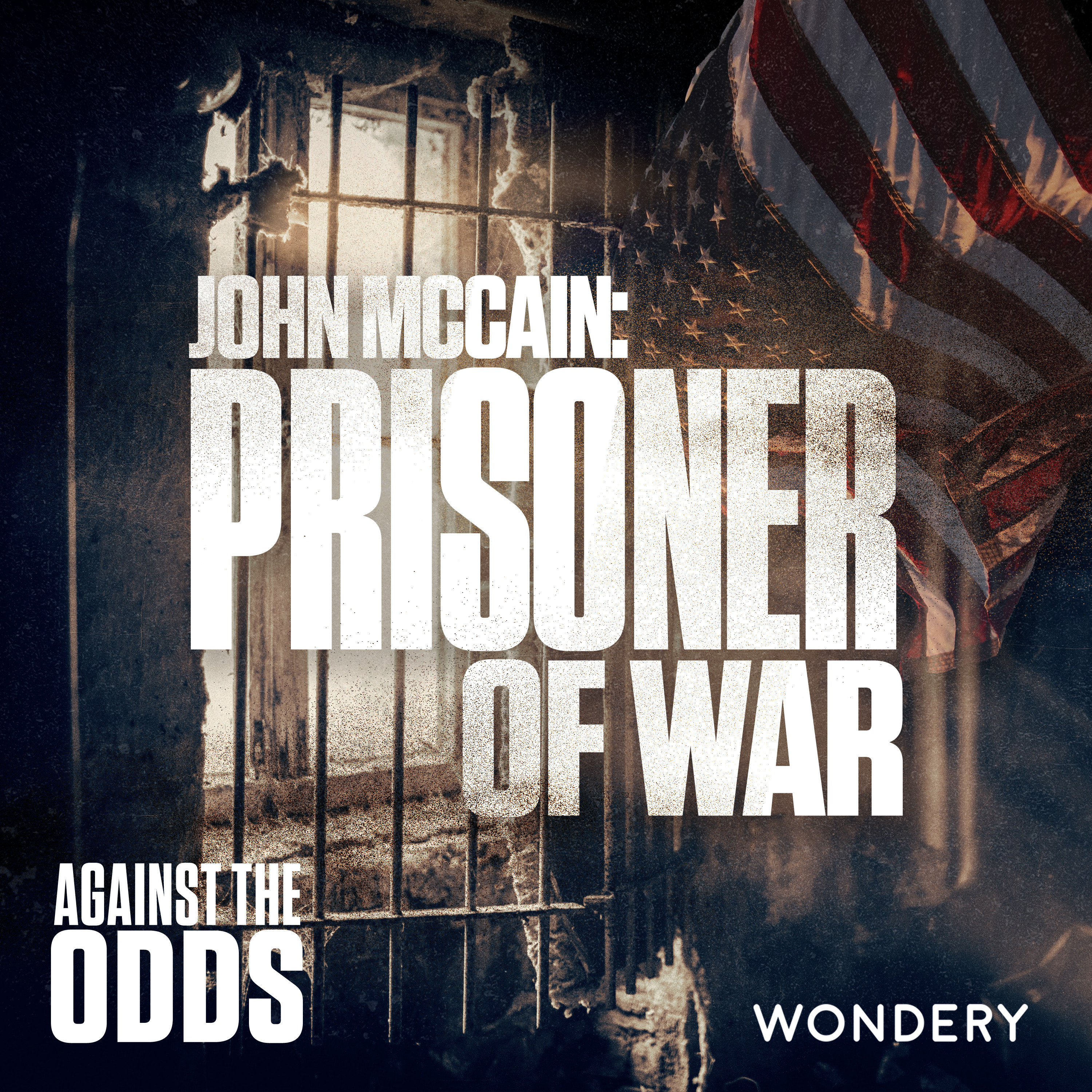
John McCain: Prisoner of War | Interview with Doug McCain and Everett Alvarez | 5

Against The Odds
Deep Dive
Shownotes Transcript
约翰·麦凯恩在北越当了五年半的战俘。约翰的儿子道格·麦凯恩和在河内希尔顿监狱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战俘埃弗雷特·阿尔瓦雷斯讨论了越南战争对其生活及其所爱之人的影响。更多阅读,我们推荐泰勒·鲍德温·基兰德的《河内希尔顿的教训:高绩效团队的六个特征》。请参阅 art19.com/privacy 上的隐私政策和 art19.com/privacy#do-not-sell-my-info 上的加利福尼亚州隐私声明。</context> <raw_text>0 来自Wondery,我是迈克·科里,这是《逆境求生》。今天,我们将结束我们的四部分系列节目《约翰·麦凯恩:战俘》。
大多数人认为约翰·麦凯恩是一位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但约翰也是一位海军军人,他在越南一个名为河内希尔顿的战俘营中幸存了六年。他经历了酷刑和长时间的隔离。他被拒绝获得医疗护理,并幸免于难。许多人说,他作为战俘的经历是他形成性格的重要部分,并促成了他成为一位忠诚的公务员。
今天我有两位嘉宾。首先,我有道格·麦凯恩。道格是约翰·麦凯恩的长子。他既是海军飞行员,也是商业航空公司飞行员。道格,感谢你的到来。乐意之至。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是埃弗雷特·阿尔瓦雷斯。埃弗雷特是一位前美国海军军官,在越南被俘3113天。
作为战俘,这是任何战俘中最长的服役期之一。从那时起,他合著了两本关于他经历的书,后来在罗纳德·里根总统领导下担任和平队主任。感谢你的到来,埃弗雷特。
乐意之至。能请到你们两位今天来,我深感荣幸。我想我应该先问问,你们两位以前见过面吗?是的,当然。天哪,我第一次见到道格的时候他还是个小伙子。道格,你父亲回家的时候你几岁?我大概13岁。我认识阿尔瓦雷斯指挥官很久了。
是的。我们回家后,我更了解约翰了。我在华盛顿。我在里根政府工作。约翰当时在国会。所以我们经常见面,也认识了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安迪和他的妹妹。我们先从埃弗雷特开始。我知道你直到获释后才遇到约翰·麦凯恩。对吗?不。
不,不。我在河内希尔顿见过约翰,但直到战争接近尾声时才见到他。当俘虏开始让我们更多地交往时,我遇到了他。人们开始到院子里去,可以自由活动。那时我遇到了约翰。而且
当然,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你们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被关在一起。你们被单独监禁。但我发现这个逆境求生的故事中许多令人着迷和感动的事情之一是,你没有人可以交谈,但是……
美国战俘能够通过相邻的牢房互相交谈,对吗?在河内希尔顿。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那方面的情况吗?嗯,我们很早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是第一个在河内希尔顿被击落的。大约九个月后,另一次早期坠机事件带来了这种知识,我们称之为“敲击码”。它是,呃,
通过敲击牢房的墙壁来利用,这样声音就可以在墙壁另一侧的其他牢房中听到。它类似于摩尔斯电码,但我们能够利用它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通信系统,因为营地指挥官的一条规定是牢房之间不允许进行交流。
但这对我们来说行不通。所以我们能够广泛地使用它。这真的是我们拥有的生命线。它让我们团结起来,因为它让我们保持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继续前进。是的,毫无疑问,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对吗?
哦,绝对的。我们分享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传递了传记。我们传递了谁在哪个营地,谁在哪个牢房。
谁在河内希尔顿的哪个建筑或哪个部分。我们有课程,数学课程,人们通过墙壁传递。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事情,我们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越南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阻止的事情。是的。约翰·麦凯恩写道,与其他囚犯交流的能力,他说,仅仅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没错。没错。
这是我们的生命线,对吧?对那些被隔离、被单独监禁的人来说尤其重要。所以,道格,你的父亲约翰·麦凯恩实际上是用这种代码与人交朋友的。你还记得约翰有没有谈到过这个吗?他谈到过一些,然后其中一些人来看望我们。我认为在他身边待了很长时间的最值得注意的人可能是鲍勃·克雷诺尔,克雷诺尔上校。
我知道他们有很多交流。我听到一个非常感人而美好的故事,你在你父亲的葬礼上敲击了他的棺材。是的。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做的?我只是认为这是恰当的事情。我在竞选期间与一位名叫杰里·科菲的先生共度了一些时光,他成为一位非常好的励志演说家。他会在这个竞选讲台上发表演讲。
他会把敲击声包含在他的讲话结束或开始和结束时。我只是认为这是告别的一种合适的方式。所以你的父亲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我认为像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想到的是他的公众形象。但我喜欢在过去几周阅读这个故事时,了解到全貌,并了解到他年轻时的个性。你还记得他去越南之前的情况吗?哦,
我只是记得他总是成为关注的中心。我的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回忆是,我还记得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一台黑白电视上观看他参加《危险边缘》节目!亚瑟·弗莱明是主持人。从五岁、六岁,无论多大,他赢得了一集。然后在下一集,他在最终的《危险边缘》中失败了!错过了关于《呼啸山庄》的问题,这
我认为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这都困扰着他,因为他是一位美国文学狂热者,而且他误解了这个问题。他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是,你知道,爸爸总是……
他从小就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你还记得他去越南的那一天吗?我不记得他离开的确切日期。但我记得更多的是,他之前已经去过那里一次了,在森林停泊处。我们实际上在纽约。但当我们在纽约的时候,他们在越南海岸的森林停泊处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火。我的意思是,数百人丧生。
他们不得不把船带回港口。所以后来他最终回到了他父亲驻扎在伦敦的地方,然后最终回到了美国。在那之后不久,他自愿回到越南。然后在那次部署中,他在奥里斯卡尼号上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就被击落了。
但我记不起他离开那次部署的日子。但他很久都没有回来。你妈妈是怎么说的?嗯,我们发现他被击落的那一天,我从外面走进厨房,她正坐在厨房的桌旁哭泣。我说,怎么了?她说,嗯,你父亲今天被击落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还记得那天,因为那天是我短暂的童子军生涯开始的日子。街上的一个邻居带我去参加了那次活动,因为她感觉不舒服。但由于他父亲的身份,我们比许多人幸运得多。到那时,他的父亲是太平洋总司令,指挥太平洋所有部队,空军、陆军、海军等。
所以越南人很快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我们几天后就得知他还活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许多家庭多年来都不知道这一点。
是的,我无法想象当你发现他还活着时,你内心会产生多么矛盾的情绪,但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吧?那一定是一种折磨。是的,信息匮乏。我们偶尔会收到一封信。
但并没有多少交流。我的意思是,我们都通过红十字会寄信,寄包裹,里面装着糖果、烟草之类的东西,希望它们能到达。我认为没有任何包裹到达过。你知道河内希尔顿吗?你听说过关于他在越南被关押地点的任何细节吗?我们没有听到太多。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有一次曾有过营救尝试,但我所知道的大部分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再来说说阿尔瓦雷斯指挥官。所以约翰被击落了,但你说你是河内希尔顿的第一人,对吗?1964年8月5日。在我被击落的前一天,我参与了现在被称为东京湾事件的事件。当时,我们两艘驱逐舰在夜间遭到
北越鱼雷艇的袭击。因此,国会通过了
东京湾决议,这实际上开始让我们军队参与其中。然后作为报复,第二天我参加了我们对北越的第一次袭击,我被击落了。所以我被关押在海防以北的当地地区一个星期,然后被带到河内,带到这座建于19世纪70年代左右的旧
监狱。这是他们在河内的主要罪犯监狱。一片荒凉。是的,有很多老鼠。它们在监狱里到处乱窜。
后来,当人们第一次被俘虏并带到河内和监狱时,我们给几个部分起了名字。他们会被关进一个我们命名的部分,但这个部分被称为“伤心酒店”,因为那是酷刑开始的地方。
对这些人进行了审讯,所有在我之后的人。我们给另一个部分起了名字,叫拉斯维加斯。我们给拉斯维加斯的酒店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星尘、凯撒宫,诸如此类。这些牢房是七英尺乘七英尺见方,
两张水泥床。你可以转过身走三步,你就会到达另一端。狭小的牢房,有时他们会把两到三个人塞进这些牢房。
还有一个部分,我们称之为“团结营”,因为那是1970年圣特袭击之后,他们把所有囚犯都带进来,把我们关进河内希尔顿。所以我们称之为“团结营”,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走到一起,巩固了组织。生活在大型群体中。就像我说的那样,从1965年到现在,这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地方。
1969年,所有虐待行为都在发生。当1965年开始拥挤时,越南人仍在将监狱用于他们的平民囚犯。所以他们开始在不同地区开设其他战俘营。
但总的来说,每个营地的待遇与当时的情况是一致的。营地里的每个人都主要为了宣传而受到酷刑。然后这些酷刑会一个个进行,然后他们会让我们独自待上几个月。
然后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清洗,然后又开始了。我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地抵抗,但不要抵抗到我们被彻底摧垮的地步。一旦巴黎和谈开始,越南人意识到我们是一种宝贵的商品,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将成为谈判结果中一项重要的资产。所以我们的待遇逐渐好转。
直到最后。战争结束时,我们有500人从北越和老挝出来。然后大约有90人从南方出来,那些在南越幸存下来的战俘。从北方出来的我们大多数都是被击落的飞行员。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说,那些在河内希尔顿的人都是飞行员、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我可以问阿尔瓦雷斯指挥官关于“后卫行动”的问题吗?我会告诉你,那始于1972年。实际上,“后卫行动”我认为始于夏季
但它加剧了。尼克松总统所做的是发射他拥有的武器,因为他的目标是结束这一切。我们结束这一切的唯一方法是迫使北越政府投降。
1968年,当巴黎和谈开始时,我们的希望真的升高了。我们逐渐意识到,这将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迫使这些人认真谈判并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狠狠地轰炸他们。所以在1972年夏天,
尼克松总统恢复了对北越的轰炸,这是伟大的一天。我们在一个叫做“动物园”的营地里。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响起。飞机开始在我们周围开火。然后他开始轰炸河内周围的军事目标,我们终于说:“该死的时间到了。”
1972年的选举,是越南人的宣传,发言人会谈论这件事,我们会仔细倾听,因为这是很好的信息。就在那次选举之后,他们开始认真地轰炸。我的意思是,每天晚上,B-52轰炸机来了,我们所在的建筑物,大型牢房的屋顶,灰尘会飘落下来,小颗粒。
如果它们掉下来,我的意思是,它们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我们试图保护自己。然后在1972年圣诞节后的晚上,一切都停止了。
大约两周后,越南人把我们叫到院子里,他们宣读了巴黎和谈的结果和战争的结束。我们第一次有了装满土豆和食物的货车。我个人体重很长时间只有110磅。但当我们从那里出来时,我的体重是140磅,我的正常体重是160磅。
哇,减掉了很多体重。埃弗雷特,我必须说,我一直闭着眼睛,生动地描绘着你所解释的一切。你是一个很棒的故事讲述者。我不能说得太多。我想回到你说的一个我无法摆脱的事情,那就是大约七英尺乘七英尺的牢房,基本上只能躺下。
你能谈谈你是如何在逆境中应对的吗?再说一次,播客的重点是人们在必须的时候可以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被俘虏之前,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被关押在这个叫做越南的陌生的外国土地上。
河内的一座监狱,周围环绕着警卫和审讯人员等等,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意识到,我的上帝,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国家,半个世界都在周围,我的同事和同龄人都在船上,在海上。这是一场战斗。这只是为了保持
我的清醒思维的一种战斗。我受到宣传、他们的历史等等的冲击。这非常困难。所以我必须保持我的想法,我做了很多祈祷。另一个重要的是意识到如何保持我的身心健康,尽管这很难。所以拥有
一直被单独监禁。然后后来其他囚犯开始进入牢房,但我仍然独自一人在一个七英尺乘七英尺的牢房里待了大约六个月,然后我才加入其他人。
也很困难。你意识到你必须做一些事情才能尽可能地生存下去。我开始做一些在精神上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来保持我的思维,因为我知道这很重要。然后尽我所能保持身体健康,即使你被限制在一个七英尺乘七英尺的牢房里。
有一些事情,比如俯卧撑、仰卧起坐和原地跑步。我自己没有做那么多,但是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被限制在那些狭小的空间里时,我们会进行比赛。
你做的一些精神练习是什么?我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比如设计电路、设计房屋、金属游戏,比如记住所有班级、所有学校,以及谁在哪个班级,名字和他们的家人。然后后来,当你幸运地有一个人在墙的另一边敲击时,你通过交流和保持生命线来互相鼓励,就像道格说的那样。
你知道,你会打电话给他,说,点,点,点,点,点,他会回过来,点,点。是的,顺便说一句,越南人永远也学不会怎么做。所以要保持希望,你尽你所能保持士气。而且似乎也有一点幽默感,给这些地方起了希尔顿的名字。在最黑暗的时刻和最糟糕的时刻,你必须有你的幽默感。
我的意思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受到了惩罚。我和我的两个室友被戴上了脚镣,然后我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
这很艰难,他们每天会让我们出去10分钟。有一晚,我们正在挣扎,尽我们所能。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开始大笑。我们笑个不停。我们会说,你知道,家里的人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我想象得到,在这种共同的经历中,你和这些人建立的联系几乎是牢不可破的。
道格,当你听到这些传奇人物讲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时,你有什么感觉?感激。
人性化。自豪。主要是自豪。埃弗雷特,再让我们回忆一下。你是营地里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战俘。那究竟有多少天?八年半。3100多天,但谁在乎呢?我不是历史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人。在南越,越南有一位同志。
在我被击落前的六个月,他实际上幸存下来并在1973年回家了。但我是在河内希尔顿的第一人。你还记得你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约翰·麦凯恩吗?是的。
那是当他们,你知道,让我们走出牢房,我们正在交往,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牢房来回走动的时候。我记得站在我的牢房前面,我看着院子,这里有一个牢房,这里有一个家伙。那时他有着令人震惊的白色头发,他的胳膊,你知道,很奇怪。他们
事实证明,它们断了。他站在牢房门口,每一个走出来的人,他都在拍他们的背,和他们说话,和他们握手。每个人,你知道,来来往往。我对旁边的人说,我说,那个家伙是谁?
你知道,站在那里说话。他说,哦,那是约翰,那是约翰尼·麦凯恩。所以我记得看着他说,我告诉旁边的人,我说,那家伙将来会成为政治家。看着吧。如果他不是,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二手车销售员。嗯,其中一个非常接近正确。是的。
所以,道格,当这一切都在越南发生的时候,你和你的家人在家里听到了关于你父亲的什么消息?我们没有听到太多。我想,也许整个时间只收到过两封信。我们唯一的一次或真正的一次交流是在他被俘虏的早期。
在越南人弄清他是谁后不久,他们对他进行了伤势治疗,并把他放在河内的一个简易医院病床上。镇上有一位法国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最终在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中播出。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太多。我们只是希望一切顺利。你是如何保持希望的?你知道,在那段时间里,我唯一的一次挫折是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在圣诞节期间去费城郊区探望她的父母。圣诞节前夕,她从探望她的朋友康妮和萨姆·布克宾德回来。
他们在费城拥有一家著名的餐馆。她曾与康妮上过大学,她发生了一起可怕的车祸,在布林莫尔医院住了六个月,这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你母亲发生了一起可怕的车祸。你的父亲在某个地方,不确定在哪里,但你知道情况不好。这两者都是,我的意思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持结构。你一定感觉你的生活正在崩溃。不。
不。我的意思是,你仍然有朋友和其他家人以及一个社区。我们继续做事情,祈祷一切顺利。这真的是你唯一能做的,对吧?我无法影响那里的结果。但我仍然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我想强调这一点。非常幸运。非常,非常幸运,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知道他……
由于他父亲的身份,他几乎立即就活了下来,而且他回来了。我认识那群人,奥兰治公园,我们居住的地区有很多,你知道,海军和空军的飞行员家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都有来自那个群体的朋友,他们的父亲从未回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父亲会告诉你,或者他确实告诉你,在他被诊断出患有胶质母细胞瘤后不久,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是。我的意思是,他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湾坠毁飞机后幸存下来,在森林大厅的可怕大火中幸存下来,并且在早晨幸存下来。所以,你知道,我很幸运。
飞行员是滑稽的人,迈克。我们是一个滑稽的群体。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与普遍看法相反,海军飞行员能够做到敏感、有爱心和关心。但不幸的是,他们唯一能这样做的人是自己。我们会开玩笑,阿尔瓦雷斯指挥官……
阿尔瓦雷斯会告诉你这一点,我们会对任何事情开玩笑。我的意思是,他谈到了他们都开始大笑的那一夜。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越界的。什么也没有。
所以我想问你们两位一个关于回家和战后生活的问题。但首先,在这个故事中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是,被囚禁如何与其他战俘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友谊。所以,道格,我知道你说你父亲没有说太多,但他有没有谈到过战争中具体的某个朋友?
直到他们来探望后,他才具体谈论他们。我认为他当时最亲密的朋友是鲍勃·克雷诺尔。但还有许多其他人来探望。我必须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一秒钟。获释后,你是否与其他任何战俘保持定期联系?
哦,绝对的。我们总是与这个人或那个人保持联系。我的意思是,一周不会过去,我没有与其中至少两个人联系。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认为这样的经历会让你和这些家伙的联系比超级胶水更牢固。世界上最大的粘合剂将是这种经历,共同分享,最终能够幸运地离开。
让我们谈谈回家吧,伙计们。我们简要地谈到了这一点,但道格,你能告诉我们你父亲约翰·麦凯恩回家的那一天吗?你还记得那一天吗?哦,我记得那一天。我不记得日期。有趣的是,我昨天踢足球时摔断了腿。
我摔断腿的那天晚上,他们宣布了一项协议,你知道,战俘们要回家了。所以几个月后,他们释放了所有人。我还记得在电视上观看,埃弗雷特显然是第一架离开飞往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机,你知道,然后一两天后,突然有一天,两天或三天,
他们把他们都送到了菲律宾。他们把每个人都留在那里进行身体和精神评估,让他们了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例如,你知道,我父亲不知道他的妻子发生了一起可怕的车祸。一些在那里的人,他们的妻子与他们离婚了。但最终几周后,有一群来自杰克逊维尔地区的战俘,包括我父亲,他们都下了飞机,
皮特·肖普费尔,他是高级军官,发表了讲话,你知道,配偶们先上了飞机拥抱和亲吻。然后每个人都下来了,你知道,已经安排了人来照看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其他家庭也是如此,这样,你知道,各种母亲和父亲、丈夫和妻子可以重新联系,对吧?
然后生活重新开始。最终再次拥有父亲在你的生活中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好。他参加了我们很多体育赛事等等。但与此同时,他也试图……
你知道,弄清楚他将要从事什么职业。许多这样的人,尤其是像埃弗雷特这样的人,他在那里待了八年,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海军,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指挥权。所以他们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五年多了,六年多了,七年多了,我没有见过这些人,你知道,
这是一个艰难的局面,因为我现在13岁,他是我的父亲。但我心想,好吧,我不确定你会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的意思是,你不在身边,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傲慢地说。我只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是尊重他,他是老板。但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适应期。
我认为这几乎可以适用于每个人。埃弗雷特,离开这么久后回家是什么感觉?你挣扎过吗?有什么不同吗?当我回家或我们回家时,我对一切都感到非常不安。
我将在家中找到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在我获释之前,我已经收到了我结婚的消息,这已经结束了。所以当我下飞机时,我被我们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接待震惊了。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听这种宣传,这种宣传被灌输到我们的脑海中,关于反战运动。
在家的活动,人们反对战争,世界上每个人都反对美国和美国士兵。我没有准备好获得瞬间的名人地位。我的意思是,当我们下飞机时,摄像机在那里,人们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学会如何处理。
尤其是在我们回家后,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我的意思是,我被邀请参加活动、招待会、聚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明白我不必对所有事情都说“是”。这在身体上是不可能的。我当时正试图取悦人们。所以,首先,我学会了说“不”。
其次,我了解到,如果我保持这种速度,我可能会把自己逼死。战俘的经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真的很希望我有更多时间和我的父母、我的家人在一起,听听他们那一边的故事。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有机会坐下来谈论它。我太忙了,到处跑,
然后,当然,重新回到现役,然后遇到我的妻子。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德克萨斯州。我急于赶上并做事情。我决定在20岁退休。
就像道格说的那样,我从未有过指挥权。我退休并离开了海军,立即被里根政府吸引。就像你之前提到的那样,我担任和平队副手大约一年半。然后我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二把手。在那里我更了解约翰。在那之后,我开始自己的事业。最后,由于疫情,我被迫待在家里。
生活只是过得太快了,很多好事都发生在我身上。很多大门都打开了,很多机会。好吧,从越南到美国的过渡听起来就像一拳打在脸上一样温柔。我的意思是,那里实际上将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埃弗雷特和所有这些绅士回来的国家与他们被击落时和回到美国时相比,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人们在吸食大麻和服用LSD。而且,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同的事情。
约翰写了一本回忆录,名为《我父亲的信仰》。显然,他和你的祖父、他的父亲杰克的关系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我很想听听你父亲和你祖父杰克·麦凯恩的关系。你的祖父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人,每天很早就起床。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他在二战期间是太平洋地区的一名潜艇舰长。
这可不是胆小鬼干的。他显然在海军中晋升到了很高的军衔。我认为首先,我的父亲,他对他的父亲所做的事情和他祖父之前所做的事情的尊重。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的父亲的海军生涯,是一种相互尊重和钦佩的关系。
但我确实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你知道,一旦他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他父亲和祖父取得的成功,这促使他不会失败。所以,你知道,杰克·麦凯纳,我记得我和我父亲坐在一起问一些关于在太平洋发生的事情的问题。
这总是很有趣。我可能从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士兵对海军或我们的任何部队来说有多么重要。你知道,是士兵们做了苦力,是他们的辛勤工作赢得了战争,让我们安全。我的意思是,军官们做领导方面的事情等等。
让大家保持纪律。但归根结底,大部分牺牲都是由我们军队的士兵们做出的。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当你问阿尔瓦雷斯指挥官和那些在越南经历了地狱的人时,你知道,在某些时候,普通人会做出非凡的事情。
美国在其历史上一直受益于站在正确的一方。你知道,麦凯恩家族的名字及其在美国军队的参与,可以追溯到我的曾祖父之前。它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好吧,不,它可以追溯到乔治·华盛顿。但是……
那里有一个血统,我认为这是促使我父亲关注公共服务而不是商业世界的原因之一。你的父亲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担任政治家和公众人物。但你认为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关于他个人的事情是什么,他能与我们分享吗?好吧,首先,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
我多年来都告诉他,并且有一些真正参与竞选的人告诉他,你知道,说,你知道,约翰,你为什么不放弃政治去开个广播节目呢?你知道,你的影响力会更大。但这并不是他想要进入的领域。我的意思是,他非常聪明。在我看来,媒体并没有给他足够的肯定。
我认为他从战争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首先,美国是一个非凡的国家,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都认为地球上最大的希望是民主。
我认为这就是他想要留在参议院的原因之一。他的真正信念是,世界上民主越多,商业越多,受压迫人民的希望就越大。
最终冲突也会减少。我认为这就是驱使他的动力。说到约翰在战争后的感受,当然,关于越南战争有一些争议。他对这一切的感受是什么?我知道他对这件事最大的感受是,无论战争或冲突是否有争议,你都不想根据政治来做出军事决策。你要么投入你拥有的资源来尽快击败敌人,
并且伤亡尽可能少,要么你就不参与。这是一个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已经学到的教训,例如沙漠风暴一号,我们投入了压倒性的资源,它基本上立即结束,伤亡最小。他的态度是,你看,我宁愿赢得战争,
而不是赢得选举。所以我认为他在越南学到的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年轻男女派往海外并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时,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而不是一些对媒体和公众看起来不错的考虑不周的机制,而是危及他们。
所以听起来他在河内希尔顿被俘的经历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或者只是他普遍的公平感。我认为这确实让他意识到,你知道,世界各地还有其他观点,也有一些人会不同意我们做事的方式。但话虽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参与
通过解决方案或业务或任何其他方式。需要找到共同点的方法。我认为他可能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他,你知道,很可能从第一天起就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凡的国家,因此有义务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而且,你知道,
我们在二战中派所有这些年轻男子去欧洲。他们不是去拯救美国。美国很好。
他们去拯救欧洲、人类和世界其他地区。他们无私地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就是我父亲在越南战争后看待他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美国的角色的方式。我认为这就是驱使他的动力。我真的这么认为。谢谢,道格。这是一个很棒的回答。最后,给埃弗雷特。所以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像你这样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你会说关于作为战俘的经历,大多数人都不太理解的是什么?
我认为很多人都不了解我们的感受。所以我过去常说,在我们失去之前,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拥有什么。越南战争教会我们的一件事是,不要责怪战士的战争。我有机会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工作。我和很多越南老兵及其项目一起工作。
我们对退伍军人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是,他们承担了责任。公众将责任归咎于他们,这是错误的。他们把战争归咎于他们,而不是归咎于所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政客们。
好了,各位,结束了。能和你们两位交谈真是莫大的荣幸。这是一次我很快就会忘记的谈话。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两位。谢谢。谢谢。
这是我们系列节目《约翰·麦凯恩:战俘》的最后一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此事件的信息,我们强烈推荐约翰·麦凯恩的自传《我父亲的信仰》(与马克·索尔特合著)、罗伯特·廷伯格的《约翰·麦凯恩:美国史诗》以及HBO Max纪录片《为谁敲响丧钟》。我们还推荐泰勒·鲍德温·基兰的《河内希尔顿的教训:高绩效团队的六个特征》,
我是主持人迈克·科里。戴维·加德纳是我们的制片人。泰勒·基兰是我们的顾问。布莱恩·怀特是我们的副制片人。我们的音频工程师是塞尔吉奥·恩里克斯。我们的执行制片人是Wondery的斯蒂芬妮·詹斯和马歇尔·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