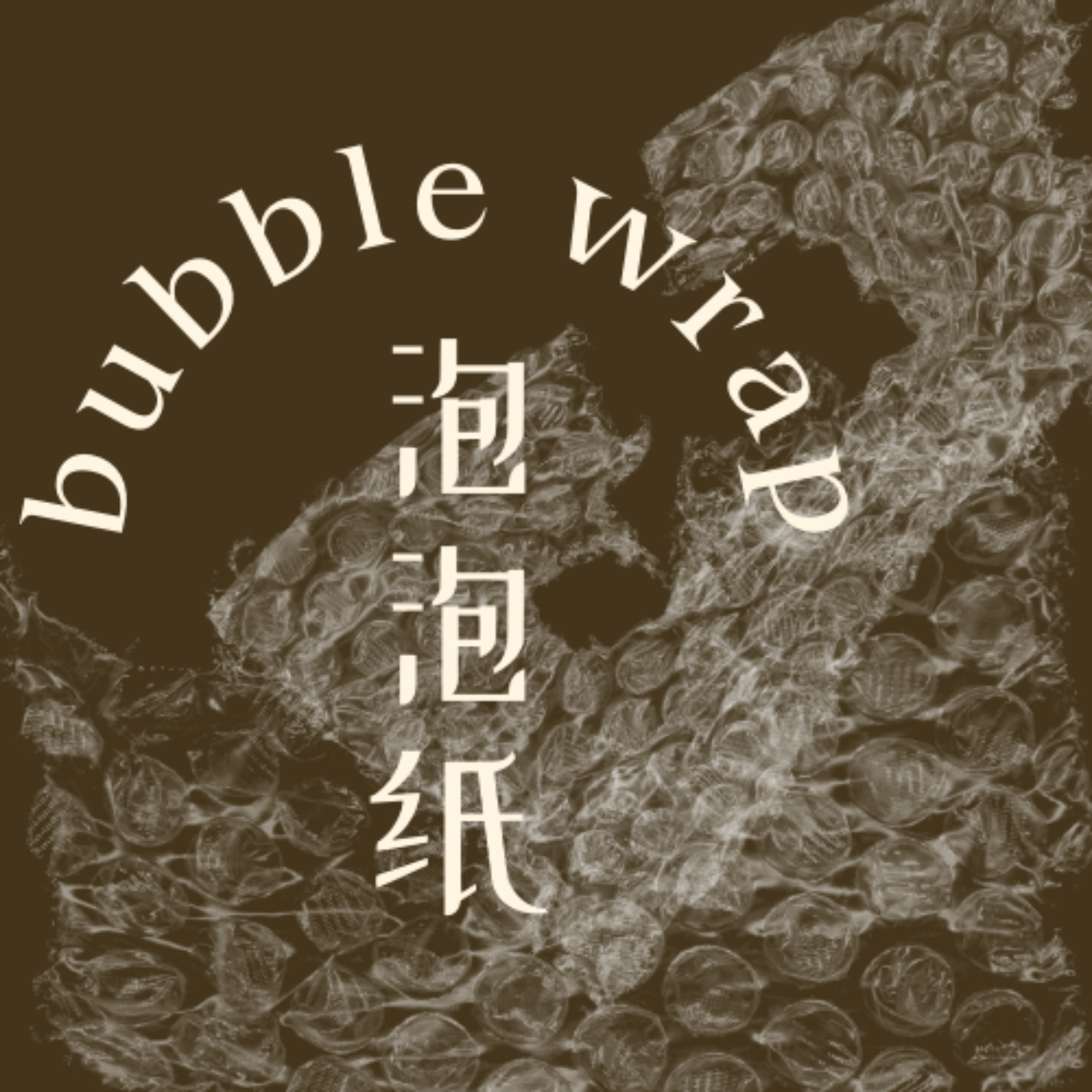Shownotes Transcript
大家好,欢迎收听 Bubble Rap 泡泡纸,我是佳怡我是兰,我们是在伦敦和洛杉矶学习生活工作的艺术策展人
在这档节目中,我们分享艺术与生活中被泡泡纸保护的珍贵时刻和带给我们捏爆泡泡纸一样感觉的解压瞬间那么这一期节目呢,是我跟嘉宜有史以来最长时差录制的 15 个小时了吧是,而且还好是那个夏令市改了美国
所以现在时差变小因为兰现在在香港是的我现在在香港然后我现在这边是晚上十一点半佳怡那边是八点半我这次来香港也主要是一个工作行程然后还有一个是 R8 走嘛所以很多世界各地的艺术行业的朋友也都会来
所以是一个艺术界的大盛世吧然后我这次也特别期待能够在香港参观 M+.从它开馆以来我就一直想要去看因为希克藏品的这个展览被分为了三期作虽然我错过了第一期但是我现在能看到他们的第二期
而且还有一件展品在展览中展出然后这个展品也相关于我们这一期要讲到的一对艺术家那就是孙元鹏宇的《老人院》对 然后我明天就计划去 Mplus 看这件作品所以也非常期待是 我其实好羡慕你因为我好想去看《老人院》然后也想去看各种各样孙元鹏宇的作品
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两个艺术家嘛这一对艺术家吧应该说其实我跟他们在这一年里有一些频繁的交叉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跟孙元鹏语相关对这对艺术家非常非常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一直
非常遗憾,然后也有一点点小惭愧的点是,我一直对孙元鹏语的艺术作品是一种远观的态度。我论文里写到了两件大作品,其实我都没有在现场看到过。
然后也很期待就是在写完论文之后,就是能真的走到苏燕朋友的作品面前去看到他们作品的样子,然后也很期待在看完老人院之后的一个反馈,但是你其实之前也有看到过老人院了,对不对?
是的对在巴黎之前讲金手子那一期的时候提到过他们当时有做一个展览叫人世间然后里面当时就展出孙云彭语的这件作品然后我特别惊喜因为我是没有预料到我能看到的
然后所以之后我也会在播客讲到这件作品的时候讲一下我的观感然后我们这一期播客其实起源也是因为我就问嘉宜嘛因为嘉宜快毕业了所以就很期待想要知道嘉宜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
然后就没有想到你写了这一对艺术家,因为我一直对他们都蛮感兴趣的,就像你说的虽然没有实地的看过他们的作品,但我觉得他们是在社交媒体上和在大众群体里面有非常多讨论度的一对艺术家,就是他们的公众关注度很高。是的,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机器手在不停地在地上产一些红色的液体那个其实就是《自圆盆雨》的作品《不能自白》这个装置然后在我们这期节目里面也会给大家讲到那其实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一开始对于他们的作品就像你说的其实是从他们的视觉张力然后包括
他们的材料张力的角度上来说就深深地被他们的作品吸引了因为从他们早期的作品来看他们经常会使用一些非常大胆让人觉得视觉和生理上都受到一些挑战的媒介比如说动物的标本然后包括人体的标本然后包括
或骨灰这类的材料然后呢慢慢的越来越了解他们的作品我发现了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一堆艺术家他们其实非常有意识的在拒绝赋予他们作品意义就比如说一个记者去采访他们说你做这件作品是有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件作品代表了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刻意的回避这个问题
他们就会说那你觉得这个作品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比如说这个记者问到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材料然后他们就会说比如说我觉得这里就是要用这个材料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材料就感觉像是完全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因为他们不赋予这些作品意义所以反而就交给观众策展人学者去
去共同构筑了他们的作品的意义和更深层的内涵然后也在不同的展览和不同的这种舆论空间里给这些作品更深层的意思然后我还记得在读他们一篇采访的时候我也在我的论文里引用了这个就他们引用了禅宗的一个题词嘛就是说普提本非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就是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也看作这种像镜子一样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人去看的时候其实都会看到自己的反射也会就是通过这个上面的一些小细节去脑补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我觉得他们的作品是在我感兴趣的中国当代艺术和我感兴趣的策展领域都有很大研究空间的这么一些作品所以其实我的研究过程和传统的艺术史研究相比我更多的会去关注到他们的展览的这个背景然后包括展览的一些
在展览的展册里面怎么去描述他们的艺术然后并且后面后面我就产生了一个质疑我就在想说真的有艺术家能够脱离意义来纯粹的创造艺术而完全不去把控作品的意义吗就是我在想说一个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时候比如说孙元鹏也的创作始于可能是 1990 年代末然后 21 世纪初那在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完全的摆脱你的时代所赋予的这些背景来完全的去创造一个跨时代性的然后可以在任何时代都不去考虑创作背景的意义吗然后带着这样的疑问其实我也去拜访了
这对艺术家然后跟他们产生了一些聊天然后在我们今天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他们告诉我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在大众的视野里面包括在媒体学者的研究里面孙元鹏女的作品是幽默是在非常严肃的背景之上的但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出发点其实
很小然后也很有意思只不过生发出来的这些媒介都是一些非常庞大且沉重的媒介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之前在上艺术史课的时候去学习如何分析一件艺术作品老师是给了我们明确的三个步骤的
第一就是 visual analysis,视觉分析,第二就是结合 context,结合他的时代背景,然后第三就是去结合前两项总结出他的作品构建出了什么样的意义,并且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隐喻。
所以可能直到现在我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和分析也都是围绕着视觉上的信息和它的背景来做一个阐释不过我觉得孙元鹏与他试图去摆脱这个 context 这个背景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非常的注重于它的物质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也很期待在今天的播客里面听你讲述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那么嘉宜要不要先大概的给大家走一下你这个论文的框架然后我们再从艺术家的这个生平和创作背景开始嗯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这个论文主要是讲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的展览场域里面他们的意义如何变化但是因为向格兰刚刚提到我们受到的这个艺术史训练而且我觉得本身分析这个作品本身的物质性和本身的这个 context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的作品大概可以分成平行的两部分我主要只分析了两个作品因为硕士论文其实它没有要求你写的那么长然后我两个作品大概每个写了 20 页左右就写完了没有那么长每个写了 20 页
很难想象如果要写博士论文的话要写上百页吧可能就是要写他们整个的这个职业背景然后我每一部分就是先分析他们这个作品本身然后呢又选了这个作品所展示的不同的展览的背景然后我选择了两个作品分别是叫一个或所有 04 年作品
然后和他所展览的三个展览以及 2016 年的无法自拔和他所在博物馆展的两个展览以及他在互联网上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病毒式的传播然后最后有一个结论所以这个论文的结构还是
然后今天我们来讲呢其实是会再加入一个他更早的作品 2000 年的人游以及 09 年的老人院也是蓝明天即将会看到的这件作品那么我们就先还是从这个两个艺术家的生平背景开始其实他们的背景
我不想介绍很多,但是主要就是想说他们两个都是 1970 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然后分别是 1972 年出生,孙岳元 1972 年出生在北京,然后彭宇是 1974 年出生在黑龙江。他们的学术背景呢,其实都是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油画。
也是在 90 年代开始进入真的艺术的这个非学院式的这种 practice 然后在这个 practice 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意识到他们其实在学院当中学习的这种绘画的基础带了太多需要被赋予意义的枷锁
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们开始想要去突破所谓意义束缚的一个开始就是因为可能他们在美院接受的油画期的教育当时还是更偏比如说你想要去表达一个和社会有关的议题然后你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标志物然后这些标志物代表了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技法去传达这些都是一板一眼的有这种框
像有一个公式一样的去搭建起来这种绘画的 practice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那个时候就感觉束缚太大了包括 90 年代也是一个中国社会巨变的时候嘛所以他们就开始接触所谓的这个装置艺术然后也开始转向更加实验性的艺术形式然后这个也是和我们之前曾经讲到过比如说八九艺术大展啊然后包括北京东村的艺术然后很多艺术家去到美国欧洲然后包括从开始有这些文化交流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其实这个创作背景呢对于他们对于创作理解有了很多的影响和变化然后也让他们开始创作的这些装置类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挑衅性他们其实一开始会被归结于叫尸体派因为他们用了很多就是人体材料包括比如说骨灰尸体人体脂肪然后这些作品其实
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了因为现在其实即使有一个艺术家想要做这样的作品你也很难去获得这些材料包括如果你获得了这些作品可能就是很少有地方敢展出这样类似的作品
这些作品就是不仅挑战了观众的伦理底线,也在当时甚至媒体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让他们迅速地成为了艺术圈的媒体的焦点。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分别创作的,在 90 年代,然后在 2000 年呢,他们才开始合体进行创作。
然后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就是现在看来包括当时当艺术媒体去采访他们的时候也会问到说比如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你想要引发观众什么样的思考你对于观众或者对于这些艺术评论人想要什么样的启发但是其实他们当时也是会绕着圈子去回答这些问题然后这次我在跟孙元聊天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向他
请教因为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一开始都会希望有一个结论但是其实我在写他们的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我很难去
引发这个结论我除了就是摆这个论据我就说这个作品可以被这样这样解读然后呢每一个场域会给他一些不同的解读的方式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从我的论文里面只能够给大家摆一个现象然后同时去提一些问题我们作为策展人在
在接触艺术家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职责我们要怎么去比如说在现在的网络社会去阐释一个艺术作品然后当它会被网络无限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很难去下一个结论然后我当时在跟这个艺术家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讲到了一个点我觉得从另一种方面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对自己艺术的态度他就说他说我觉得你这个论文其实你要做的不是玉你要做的是一块砖就是抛砖引玉的这个比喻就是说你提供的是一个框架然后呢
让你的读者也好让你的后面来的学者也好去更多的进行这个思考那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其实也是这样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基础的框架他们提供的是一些基础的材料然后呢让观众去赋予
这些作品意义,然后这些作品意义的赋予很多时候是受到比如说策展人的引导或者是学者的引导所以他们的作品往往没有明确的阐释而是留下了这个空白的空间然后留下这个框架里面你可以填的东西让后面来的人去把它填起来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试图得出一个结论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结论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个被权力化的产物就是可能不给出一个结论其实是在挖解一个权力体系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策展或者说是一个机构要去呈现一个叙事的时候把一个结论直接抛给观众有一点就是比起说直接告诉你一个结论
可能更开放式的引导观众去思考一个问题对于现在的这个艺术的可能发展的语境会更好更健康一点就是去瓦解一个大的话语结构或者说是去瓦解一个大的叙事的体系而且我今天还想跟你分享一个我在飞机上看书看到了一段给我启发的
就是我在飞机上看的是
Virginia Woolf 的那个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就是一个经典中的经典但是我想讲的不是说她聊到的女性写作的部分而是说她有一段讲到说小说和文学对她来说是什么然后 Woolf 就说小说像一张蜘蛛网看似在风中飘摇但却连接着生活的各个角落
蜘蛛网不是悬在半空中的蜘网的也不是什么看不见的生物它们从人类的苦难之中诞生和有形之物密切相关比如健康财富和我们居住的房子然后我读到他写的这个讲小说和蜘蛛网的比喻就让我觉得其实艺术也有点类似一个这样子的意象就像蜘蛛网一样然后
包括我之前在读文学作品比如说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比喻然后往往读到那些比喻的时候我就会读到他文学的趣味跟他文字中的那个艺术性引导我去
将生活的很多日常之物跟一些非凡之物做一个连接反而让我一下子开始引生发很多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艺术它有的时候它的功能就像一个比喻一样而且这个比喻它不是说我今天的心情
像太阳一样就不是这么就是简单的很让人能够一下子联想到的比喻很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很不平常的比喻但反而这种不平常的比喻会让你一下子去思考很多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恰恰也是孙元鹏女作品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你说这个比喻不管是作家也好艺术家也好是他在他的脑子里做了一个连接但是因为你的人生经历和可能时代背景和他的不同可能那个连接不是天然的发生在你的脑子里但是因为他在这个话语体系或者这个语境下用了然后这个比喻对你来说 make sense 然后你在你的脑子里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那种火花就很有意思
然后后面我们再仔细的讲这件事但是我想提在这里挖一个小坑其实在孙元鹏语做那个机器手的那个动作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那个机器手的最基础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你如果在桌面上洒了一杯水
然后你要用手或者用纸巾去拢水的那个过程就是你四面八方的拢然后那个水就会往四面八方的流它只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把这个动作提炼出来需要哪些关节需要哪些步骤然后需要什么元素然后把它分开
放到一个和日常生活完全不相干的场景里面就构成了其实无法自拔这件作品哇哦那好快来开始讲作品吧我等不及了好那我们就从最早进入正题对
最早期的作品开始讲就是 2000 年的作品《人游》这件作品是他们早期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之一严格来讲这件作品是他们在合体之前彭宇做的一件行为作品但是其实类似的媒介孙元也做过这种比较相似的装置作品叫做《蜜糖》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媒介上面达成了很强的共识然后也造成了他们后面决定去以组合的形式来做作品然后前面应该没有讲到就是孙岩彭宇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他们既是夫妻又是艺术上的这种伙伴
这件作品其实是艺术家彭宇以母亲哺育婴儿的姿态抱着一具皮肤剥落的死婴然后试图用一根管子将从人体脂肪当中提取出的油通过这个婴儿的嘴喂下去整个画面他的行为和表演都非常非常的平静就像一个母亲在正常的哺育她的孩子的状态
那么他的动作也非常非常舒缓,看似充满了母性的关怀,但是这个婴儿他其实已经死亡,他没有办法给出回应,然后也没有办法吸收这些油,这些油慢慢的会从他的嘴角流出来,然后流满整个尸体和整个的这个场地。这件作品视觉冲击力其实非常非常强烈,然后当你在看到这件作品,
就是不需要多长时间你就会意识到这件作品与正常的母婴之间的这种连结和爱不同的这个状态从而会让观众感到深深的不安其实是一个关于死亡和生命这种非常强大的反差的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我觉得我选择这对艺术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研究这对艺术家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现在就在 USC 教书,他叫郑美玲,然后他是在 USC 不是艺术史的教授,非常神奇,他是在戏剧 department 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中国行为艺术的教授。
他对这个作品的解读就是可以看作是一个艺术史学者对于这个作品的解读他说这个作品通过喂养的行为揭示了死亡的不可逆性这个死婴的身体已经僵硬皮肤剥落嘴唇紧闭无法吞咽尽管彭宇的动作模拟了一个母亲在喂养孩子
但是死亡的存在让这种行为变得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这个场景让人意识到在死亡面前人类能做的行为是多么的有限
同时呢这个作品也颠覆了就是传统的母亲哺育婴儿的这个形象这个母亲的关怀在这个场景下就变得非常的荒诞让我们也会去思考就所谓这个母性这种看似能够穿透一切的这种关怀的力量它到底有没有界限另外一个方面
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他们作品中很强的这种物质性那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除了用到这个婴儿标本之外还用到了所谓的这个人油这个材料就是从人体脂肪里面提取出的这种液体
那他也强调了就是说其实人也是有物质性的这么一个存在,人被分解成了不同的部分,然后这个人有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有一些充满神秘和浪漫化的想象当中,他会被理解成是这种生命的精华,就是这种 human essence。
但是其实这种生命的精华包括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受伤了然后流出来那种组织液然后会让我们感觉它是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其实这种生命的精华这种生命的物质并没有办法做到让这个婴儿死而复生然后再次去延续他的生命所以这种人体的物质性也和生命的终结在这一刻形成了这种鲜明的对比
但是我记得之前我记得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作品还是你这次第一次看到这件作品但是我记得我每次跟大家讲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被这件作品本身给震撼到
对,我被震撼到,你之前没有跟我讲这件作品,我刚刚还在搜这件作品的图片。就有点想到 Joseph Boyce 之前做过的一个行为叫做 How to explain pictures to a dead hair.
就是如何跟一个死去的兔子解释艺术史就是博伊斯他在一个房间里面周围全部都是艺术史的名作然后他手里抱着一只已经死去的兔子然后呢再给他讲解艺术史
我觉得就是这种呈现的形式就有点像是西西弗斯的那种推石头或者是说 Francis Alice 他那个推冰块的那个感觉是就感觉我觉得对我们人类来说我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说
我记得彭宇的这个行为作品它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黑的地方有可能是因为我看的照片都是聚焦在艺术家身上你就会感觉艺术家和他这个行为周围有一圈光但是在往外的地方是很暗的然后也会让我想到说就是我们的生命
其实就是那个有限的一圈光就是死亡和未知是更往外扩的东西是更大的那一圈黑暗的东西它一直包裹着我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会去想办法要去突破然后要去对抗这个死亡的力量但是这个过程在这件作品里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徒劳的
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通过这件作品联想到社会对于母亲这个角色附加的一些责任上的枷锁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母亲从心底深发出的那种无力感是刚刚你提到 Joseph Bowies 其实那件作品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在洛杉矶的 Broad 有一个
Bowies 的大型的展览回顾展然后他就展出了很多他的作品当中的材料和他的影像但是就是给兔子讲艺术史的这个作品好像是没有完整的影像展出因为
其实策展人我们是上周还是上上周有去跟那个策展人聊天然后那个策展人就说很担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动物保护组织觉得之前是有过这样的抗议因为动物
保护组织觉得就是这个兔子已经是一个死兔子了然后你还要就是把它用在这个艺术作品里面不断地去折磨它就是对动物权益的一种侵犯那其实孙元鹏语的这个作品包括他们的很多作品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用到的这些标本然后这些尸体
是不是对于这些材料之前的这个生命的一种侵犯然后他们触碰了这个社会当中什么样的禁忌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研究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吧但是对于孙元鹏语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一开始会对他们说我们对自己的作品的意义完全不做把控
就或者说不做产式产生一个质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类型的作品太有时代特点了因为当时他们是可以从比如说医用标本然后调态下来的这种材料当中去获得不管是他们用的这种婴儿材料也好还是他们用到了一些比如说动物的标本也好去做他们的作品的
而这些作品其实只有在当时中国这种相对有一点缺乏监管的条件下才能够形成然后现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其实一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作品二这样的作品都不可能去展出
在 2016 年 17 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件就是两个斗犬就是那种专门打架的那种狗然后他们把他们两个放在两个永远不会相互碰到的跑步机上然后这两个狗就永远一直想要冲向对方但他们永远不能真的发生这个冲突然后是一件影像就他们只做了一次这个行为然后把它拍成了影像这个影像在 Googleheim 展的时候就因为
保护组织的抗议然后必须要把这件作品撤下来所以就是这些作品我觉得是充满了时代特征的而这个时代本身会引发他们这样的思考在我看来其实是他们作品意义之一是的而且他们做这件作品并且也引发社会对于可能跟道德伦理相关的思考
思考也是他的一一之一吧嗯对的那么其实这种他们作品带给人观感和情绪上的复杂性也一直是延续在他们作品的这种血脉当中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 04 年的这件作品叫《一个或所有》
这件作品走进展厅包括大家可以先看到 show notes 里面这张图你会看到的是一根巨大的柱子斜靠在展厅的墙上
然后这根柱子大概有四米长然后可能就是一人可以环抱的这种直径的宽度走过的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比如说石灰烧成的或者大理石这种制成的这种柱子但是实际上你要去看它的作品的 label 或者是你接下来听我们讲的话它其实是用人类的骨灰制成的一个巨大的柱子
然后这个柱子靠墙摆放然后在展览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展览装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的挪动会在墙上留下一些痕迹然后这个痕迹然后这个柱子包括这个从墙边打下的这个光让这个柱子在墙上留下不同的影子本身都构成了这个作品的一些组成的部分
那其实这件作品他在一开始做的时候他本来是想希望把这个作品做成一根大粉笔然后也希望就是观众进来能够真的用这个粉笔去画一些图案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吧应该说一个是因为其实他们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的
所以它其实一挪动就很容易碎掉然后是不太方便直接去挪动和使用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在非常主动的去规避就是文化暗示这件事情因为比如说当你牵扯到要写要做什么因为有语言有符号然后不可避免的
带来一些与文化相关的这种连结和暗示这个艺术家其实希望在他的艺术眼当中去尽量的规避这些
在我们说文化暗示其实跟这个艺术语言相比它就是一种明示他们希望尽量去规避这些能够让观众一下就有抓手然后反而往另一个方向去走的这种解释的空间而去用这种更加抽象的形式来做这件作品
那其实这件作品的创作背景也是像我刚刚讲的也颇具时代特性,因为大家看到这张图也可以想象到要获取这么大量的骨灰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在我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前面有念到的这个郑美玲教授她其实在书里也有写到这一件一个或所有这件作品然后大家写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描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就是这两位艺术家他们会去中国的这个火葬场然后通过获得这个被火葬人的亲属或者家庭成员的这种许可就是 consent 的这个过程然后去获得这些骨骼
然后在这个不断 consenting 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这件作品但是就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因为和孙媛朋友有关的学术资料其实并不多然后我就在我生活的各个角落尽力的去找不同的相对一手的材料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抖音视频
然后是一个艺术媒体人去拜访孙元蓬玉的工作室,然后他们聊天,然后当中聊到了这件作品。然后他们在聊这件作品的时候也聊到了说你去哪儿获得了这么多的骨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孙元他其实就讲到说他们当时在黑龙江的时候有去各个火葬场,
然后他们发现就是说一个骨灰盒里面能够盛放的骨灰是一个人烧下来的骨灰里面非常小的一部分然后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能够盛放下所有骨灰的骨灰盒可能就是要上万块钱对于很多家庭尤其是 2000 年初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所以其实就是大多数的骨灰会在火葬场被留下来,然后要么就是可能就是去废弃了,或者说要么它是一种,因为就是人的这个骨头,然后包括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养料嘛,它可以去作为就是肥料,然后再会返回到土地里。
会卖给这种堆肥的这种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认识了一个这种火葬场的老板然后就让他们拉走了两大卡车的骨灰然后完成了这件作品所以就是在他们跟中国
中国的艺术媒体人和这个来自美国的艺术史学者描述这个获得物料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偏差就是你不知道这些作品具体是这些材料具体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其实带着这个问题我在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也问到了就是这个差异嘛因为这个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你没办法就让它这么滑过去然后我就问到他然后他就说
这个过程是就是双向并行的,因为他意识到就是说一开始他们是想要通过比如说去从这些家庭里面获得这些骨灰,然后包括他们会去火葬场门口去问这些人说我能不能要你剩下的这些骨灰。
然后他们就意识到说很多人其实在那个当下因为他们的亲人刚刚去世他们是没有就是多余的情绪空间来回答你这些问题的他们要么就是随便吧反正因为他们拿不走嘛
就是你就随便用或者说有的人会就觉得他们有毛病这种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能够扩得就是我们说的 consent 一定是就是他口头说好或者说他签一个协议说我同意而不是说你随便或者他就直接走开这种其实不能被称作一个 consent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意识到
他能够获得的这种口头砍散其实不多但是呢这个骨灰这种材料就会被当成废料就去废弃掉了所以其实慢慢的他们就从这个获得砍散的这个过程转向了就是他们能够如何去获得这些材料的这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一方面
听起来是有一些伦理上的争议然后包括如果在现在的话我觉得就他们能够获得这些材料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这个艺术创作过程当中非常有趣有意思的一个创作的背景过程
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讨论到说什么样的人可能有这个财力和物力去买下一个大的骨灰盒或者什么样的人会有财力去 afford 一个单人焚烧的这个过程就你烧下来的骨灰就是你这一个人的骨灰而没有钱的人他可能就会就很多个人一起烧然后其实你捡出来的就是大家 mix 在一起的这个剩下的东西
所以这个当中也潜在的去探讨了就是中国的社会分层包括他最后做成的大粉笔其实是把很多的独立的个体去做了一个大型的组合然后这个组合不管你把它看作是一根可以书写的工具也好看作是一个可以承重的柱子也好他们后面还做了一个版本是把这些骨灰打成砖头
然后用这些砖头来做看起来像是能做建筑材料的这种 building blocks 也好,就说这些人他从一个个体变成了抹去名字和独立性的更大的系统和更大的机器当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而且骨灰它作为一个材料一个媒介也让我就意识到一个人道非人化的一个过程就是听你刚刚讲的这个焚烧骨头变成骨灰然后呢再变成一件作品的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战争的时候
大家都要在后院里面烧铁烧锅然后熔铁然后呢去供给给政府军队去做武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把原有的一个物质它剥离了它的 context 然后呢去变成了另外一个 functionality 一个用处
这会让我非常的怀疑他骨灰原本跟人的这个连结在他的生命已经流逝的时候这个连结是否还存在是还是说这是作为一个符号他作为一个在世之人以寄托思念的一个物质但他
本身的那个根就是已经去世了这个人的连接可能也随着他的生命的消失而消失那么再把骨灰作为一个材质用到作品里面它自然而然带有的很多意义也是
我们现世的这个人所赋予它的意义是的那其实这个作品在不同的展览空间里面也有不同的解读吧或者说有不同解读的侧重点应该这样说如果你只去看它一个展览的话
你可能会就是在你的脑子里输入一种解读,但是当我们把不同的展览放在一起横向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作品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空间。可以简单讲一讲,就是 2004 年这件作品做出来,然后它就在欧洲的两个展览当中做了展出,一个是在安特韦普的展览叫天下,
这个展览的策展思路是他想挑战西方展览中对于中国艺术的既有视角要么就是强调文化差异要么就是通过强行的朴实化抹去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那天下这个展览他其实试图聚焦当代艺术家如何不仅仅
回应直接的社会语境也在探讨这些超越文化边界的人类存在的根本性的问题然后他在这件作品的展出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很强调说这个艺术家他其实在讨论的是死亡然后这个死亡它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社会意义背景下的死亡它是人类可能共同的终点或者说生命的一部分
看这两个艺术家他如何通过他们的媒介来探讨这个死亡的这个过程和你刚刚说的那种其实解离的这种感觉然后跟他相对的其实同年里昂少年展的主题叫 The Monk and the Demon 它叫僧侣与恶魔那其实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那种感觉
他这个展览呢他想说他就是完全把它反过来他不想把中国当代艺术看作是一个整体去就是比如说他就回应全球化也好然后他受到西方的影响受到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好
而是去讨论就是个体性的艺术家如何在他们每个人不同的语境下去实践并探索自己的艺术创作的道路所以就他们把这件作品看作是孙元鹏与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背景下去对于这些材料对于这个问题一个非常非常独特和个体化的这么一个回应那其实
就是这样看下来这两个展览虽然听上去他们的策展思路完全不同但是你可以想到就是一个展览在探讨就是说死亡这个问题的宇宙普世性然后这个艺术家如何发展出自己的解读
另外一个他们在说这个艺术家如何从自身完全独特的成长背景和发展空间来 approach 实验作品其实这两个解读放在这个作品的背景下是完全兼容甚至有一定重合度的
就我觉得这是在不断的对比这些展览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的一个特点就是即使这个展览它本身的这种规则或者宗旨是不同的但是当你把这个作品放进去的时候你强调它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它就会天然的变成这个展览语境当中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语言组成部分
然后其实刚刚的两件作品就是孙元鹏比较早期的代表作品,中间其实从 2000 年代往后,他们就开始做了一系列的作品,就是这种 hyper realistic 的这种雕塑装置,会牵扯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做出来就是他坐在那儿你就会好像感觉有一个真的人坐在那儿,
其中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呢其实就是 2007 年做的老人院的这件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巨型的动态装置它的作品构成是由 13 个以实际尺寸制作的仿真的老年男性塑像组成的每一个老年男性都神情伪迷
但外貌打扮酷似世界各地的领袖人物他的穿着都能够让你意识到这位老人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主教或者酋长将军独裁者
但是他们如此穿着打扮又非常衰败的这个老人躯体以软弱无力的这个样子坐在 13 个电动轮椅上然后那个电动轮椅呢会一直在展厅里无规律的运动的所以就会看到 13 个仿佛世界上 top.0001%的这种拥有着权力的人
像碰碰车一样被流放在展厅里面跟观众以一个非常被动的姿态在互动然后孙元鹏与这两位艺术家呢其实是以欧洲平民的这个塑像来作为这些雕塑的原型的所以这十三位权力统治者他其实是没有特别的指代的
但是我觉得观众自然而然的都会联想到我们内心心里的那个人和觉得这件作品它的讽刺的点在哪里我觉得
我当时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展厅里看到的这件作品是没有围栏的就可能跟我明天即将去 Mplus 看到的作品不太一样因为我看 Mplus 它的那个展厅里面是把作品围起来了所以其实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时候我是能非常近距离地跟这些轮椅上的老人互动打引号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如果我离他们特别近的话他们就会停下来就像是扫地机器人自动感知到了人的存在一样他们在可能系统 program 一下就是在进行一些别的这种机械化的运动这里插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在跟艺术家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有提到这件作品虽然这件作品其实不是我论文的一个部分
但是当时我是在问他们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其实一般来讲孙岩朋友的作品大型装置他会希望做三个版本然后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收藏和展出后面我们会讲到《无法自拔》那件作品其实有两件不同的版本已经被展出来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在问他就是这两个版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
他就用这个老人院这件作品举了一个例子他是说他们在把控这个作品的样子和意义的时候他只把第一次展出看作这个艺术家的工作范畴就是他会希望说他能够亲自去到现场然后装置这个作品的每个版本的第一次展出然后这个版本就是他最终交付出去的这个艺术作品
其实后面不管这个作品是被继续展出还是被收藏还是被拿到什么其他地方去就是这个艺术家他说我完全不管他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在老人院这件作品里面他们只有第一次的时候他是规定就是说每个人穿什么衣服然后每个人有什么头型然后什么什么的
后面就是只要这个展出方和他们的画廊,好像在中国和在欧洲都是长青画廊去代理他们的作品,只要他们的这个展出方和画廊去沟通,这些人可以穿就是任何衣服,好像是有一个品牌,然后想要去赞助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就可以换上他们的衣服,
或者说他有一件衣服然后比如掉了个钮扣或者坏了这个展览的人员就可以去街上买一件衣服来给他们换上就是这个艺术家他就是在他把这个作品交出去之后他就希望这件作品就是完全交出去了所以这些人不管他是像政治领袖还是像什么这种公众人物其实他都是觉得就是这个观众自己的这么一个想法你知道他就是第一次他像了政治领袖之后可能就是在观众脑子里会
刻下这个 message 不管他这些人在做什么他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有某种政治隐喻的这么一个场面哇那他这样子的交付作品的形式更像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抛砖隐喻的过程了是因为他把这个砖抛出去了之后我们怎么去隐这个喻其实这个权利就是掌握在观众和机构的手中了嗯
是的然后他们给了一个这个这样子的框架然后我觉得这个框架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讽刺式的框架我就觉得他一开始的那个政治领袖的那些衣着像是在讽刺国际政治的一种运行方式就你会看到这样一群掌握政治权力的老年男人嗯
身体衰败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我当时在巴黎看这件作品的时候当下就觉得特别讽刺的就是说哇哦
我现在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世界就是被这样一群人统治着的是的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就是他们作品里黑色幽默的那个点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很荒诞的现实但这个现实就是真正存在的
他们以这样子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或者说是悲剧色彩的喜剧上演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是让你能够感受到在荒诞的背后是一个很深沉的痛苦和愤怒的
就虽然我觉得他的这件作品视觉呈现上对我来说很多观众可能会在那里嘲弄这样子的形象和去评论这个现在的社会是多么的像这件作品里面描述的样子但是你一下子就马上能够几倍发凉或者说是有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当你意识到世界真的就是这样的时候那股凉意是从
他的这个荒诞和他这个幽默里面他的这个暗流里面滋生出来的
是的其实这件作品它和我们前面讲的逻辑也有一点点不同因为前面他们就是一直在说说我不要 suggest 这个意义然后我不要直接的有这个指向性但是其实这件作品你看到然后包括它有这么明显的就是这个服饰上的这种指向性它其实就是讽刺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直接和明显
这也是他们所有作品里面有两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分类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或者理解他们把老人院这类作品就这种直接的有政治隐喻的或者是有这种意义上的这种指向性的作品的他们把它称为他们作品里的绘画类
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和他们之前学习绘画非常类似的一种思路包括就是你去找到这些标志物然后你去把这些标志物以什么样的思路融入到你的作品当中去然后他觉得这是他们作品当中绘画类的作品
前面那些作品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些作品他管它叫装置类他装置类的原因是因为他遵循的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他希望把一个简单的
甚至是有一点像物理或者现在科技领域里面说到所谓第一性原理的那种原理就是他把这个东西最本质的原理给呈现出来但是以艺术的方式去做一个演绎但是这个演绎它是不带有任何的指向性的每个人走进来都可以把它用到不同的领域或者是产生自己不同的理解
那这个就让我们来到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最后一件作品就是 2016 年的这件《无法自拔》然后这件作品其实是他们第一次为了在伍文海姆的这个故事新编这个展览当中展出做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机械装置然后这是一个机械手臂在一个大型的透明围栏里面不断地去清理地面上的红色的液体
然后呢这个机械手臂它的动作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像扫水一样把这个红色液体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去操控它的其实是在这个围栏的顶部有一个监控系统然后这个监控系统监控地上这个红色液体扩张的范围然后一旦超过某个范围它就会去指挥这个机械手臂把它给拢回来然后因为它用到这个红色液体
看起来非常像血液,所以其实也会让我们和人体和人的感知有一个天然的联系。包括后面在这个 TikTok 上疯狂传播的时候,很多人也会把它解读成为他在往自己的身体里加就是给他身体功能的这个机油也好,还是他自己身体的这种精华 essence。
血液也好然后让他自己机械的手臂的身体能够维持一个运转但是维持运转就意味着他要不断地工作这也是就是在 TikTok 上面非常引起就是牛马生活的共鸣的过程每天牛马然后但是如果你一旦停止工作你就会没有东西吃然后你也没有生活这种来源所以在后面就是引发了这么一系列在网络舆论环境
当中的这个讨论但是在一开始呢其实这件作品它的生发点我们刚刚已经反复提到了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包括它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它会训练这个机器手去做一些除了在不断地扫水之外其他的动作就是当它那个上面的监控没有监控到这个液体扩散超出范围的时候这个机器手就会做一些非常悠闲的比如说
摆手啊打招呼啊这些动作这是 2016 年的这个版本那其实在 2019 年的时候这件作品也出现在了威尼斯双年展当中在这个版本当中呢他把这个机械手做了进一步的升级这是这个作品的第二个版本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这个机械手除了扫水之外他除了会挥手然后除了会有一些就是左右摇动的动作之外他加入了几十个不同的动作库就让这个机械手变得更有趣其中就包括比如说他希望模仿太极和功夫的这个韵律让这个机械手进行一些非常慢动作的这种小动作就感觉是一些艺术家自己的这种
小趣味吧在这个里面加进去的让这个仿佛西西弗斯一样的这种荒谬的循环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而且我觉得也渐渐模糊了观众跟机械手之间的这个人与非人的边界是的
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就是它其实在第一次展出的时候被这个展览非常非常强调和放大的是整个的这个监控系统因为上面有一个监控然后呢这个手不停地在扫水回来然后这个展览其实也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
边境然后关于移民关于这种整个的政治监控的这种这种话题和这些讨论然后这个展览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个展览里面它承担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不仅讨论的是比如说我们时刻在被监控着然后有一个大手时刻会把我们捞回就是
我们政治上我们属于的地方而我们不能就是自由的去行动或移动然后另外一个他也在强调就是说这种监控的三维特性就它不仅是地面的它现在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三维的就是天空中时刻有人在看着你甚至宇宙里时刻有人在看着你这种感觉就是它的政治性在这个展览当中
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呢,这个政治性的强调完全是这个展览和展览策展人在这件作品当中看到的,并且觉得这件作品的艺术语言可以为他们所做的贡献。
那其实《威尼斯双年展》就更多的是展示了这个作品本身的这么一个特点和它可以被多重解读的这么一个空间再到 2021 年其实是疫情之后嘛就是在美国已经算是就是完全开放疫情之后然后这个作品再次在这个社交网络上走红已经距离这个作品在实际的物理展览当中展出过了两年的时间
然后最初开始走红的一个视频是他切了两段视频第一段是这个作品在古根海姆展出的时候就是他还动得很快然后他一会儿给你挥挥手然后一会儿扫一扫那个水然后第二段切的是他在威尼斯双眼展展出的那个片一个视频片段就是这个鸡儿手走得很慢并且应该是到展览的后期他周围的透明的玻璃罩上都已经溅满了红色的液体
包括它的地板已经斑驳了它动作慢到让你以为它就是被锈蚀了的感觉他把这两个视频切在一起说这个机械手已经过分劳累然后过度劳动已经慢慢的就是要走向这个机器的死亡了但是实际上首先这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就是这个机器手不是从 2016 年一直运行到 2019 年然后造成了这个机械的放慢和死亡
而是就是两个不同的设计而且另外一方面其实在看社交网络上对这件作品的解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肯定就是看不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看不到的那些高空监控的系统在社交网络的这个语境当中就不会出现然后包括它会过度地把这个机械手拟人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机械手产生强烈的共情去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
甚至后面就是有人会开始模仿这个机械人的行为就比如说我看到几个很好笑的有一个是说有一个人开着挖掘机然后在自己周围那个挖沟然后就把自己周围的土都挖了然后挖着挖着就是已经挖不动了然后边上沟外面的土越来越多然后沟越来越深就把自己困在了这个沟的中间然后包括什么扫实验室里地上的水啊这种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啊对
对,就是他其实在这种解读的背景下,他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他不知道有监控系统,他不知道有动作库的升级,他甚至不知道这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作品,就是一件作品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然后是新的机器,然后包括这个机器只运行三个月,是完全不会对这些工业级的这种机械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的。
但我觉得就是在情感投射这方面真的网络环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入口去看就是观众如何能够把自己和这个所谓艺术品或者这个机械的边界基本上就是拿掉了然后把自己的情感
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投入到了这个机械上让这个机器其实变成一面镜子让你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家有多么的 burn out 然后大家有多么的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疲惫还要不停的在做这些工作和这些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劳动其实这对艺术家就像是抛出了一个意象然后让这个意象
肆意地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发是对的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也问这些艺术家我觉得就是你们不在意就是学者或者是这种策展人去解读你们的艺术是你们的选择但是你怎么看就是网络上的这些艺术然后其实他们也
不介意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解读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镜子反射出来的社会一个切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就是最后我的论文就是会回到说比如说我们作为策展人
我们怎么在物理空间和网络世界当中做这个平衡但是其实我觉得孙元鹏的作品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窗口去观察到这种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这种对于意义生发和意义传播的这么一个助推的这个作用而
我们作为艺术世界的工作者策展人艺术史学者也好然后包括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也好会让我反思吧就是你在看到一个作品中你的理解是跟你的经历或者是你的兴趣的哪一个部分发生了连接而产生的这个意义和你的解读是的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看完可能 show notes 里面的图片或者了解到这一对艺术家的作品之后你们的解读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我们呢也从这周开始开设了小红书的账号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搜索 bubblewrap 泡泡只关注我们
我们会在小红书上面更新每一期的 show notes 然后包括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更新一些录播客的幕后故事然后有一些可能更适合在小红书上发布出来的展览推荐艺术推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希望在小红书上能够和大家继续分享
然后我们也会在小红书上建立一个听友群在这个群里面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我们播客里面讲到的内容包括分享你在生活当中看到的艺术或者展览甚至比如说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群里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看展搭子或者是艺术上的朋友那么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去关注我们的小红书然后也在小红书上跟我们继续聊天吧那么今天的 bubble wrap 就到这里啦也希望你能订阅我们点赞转发这期播客你可以在小宇宙 Apple PodcastOvercast 和 Spotify 听到我们的声音拜拜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