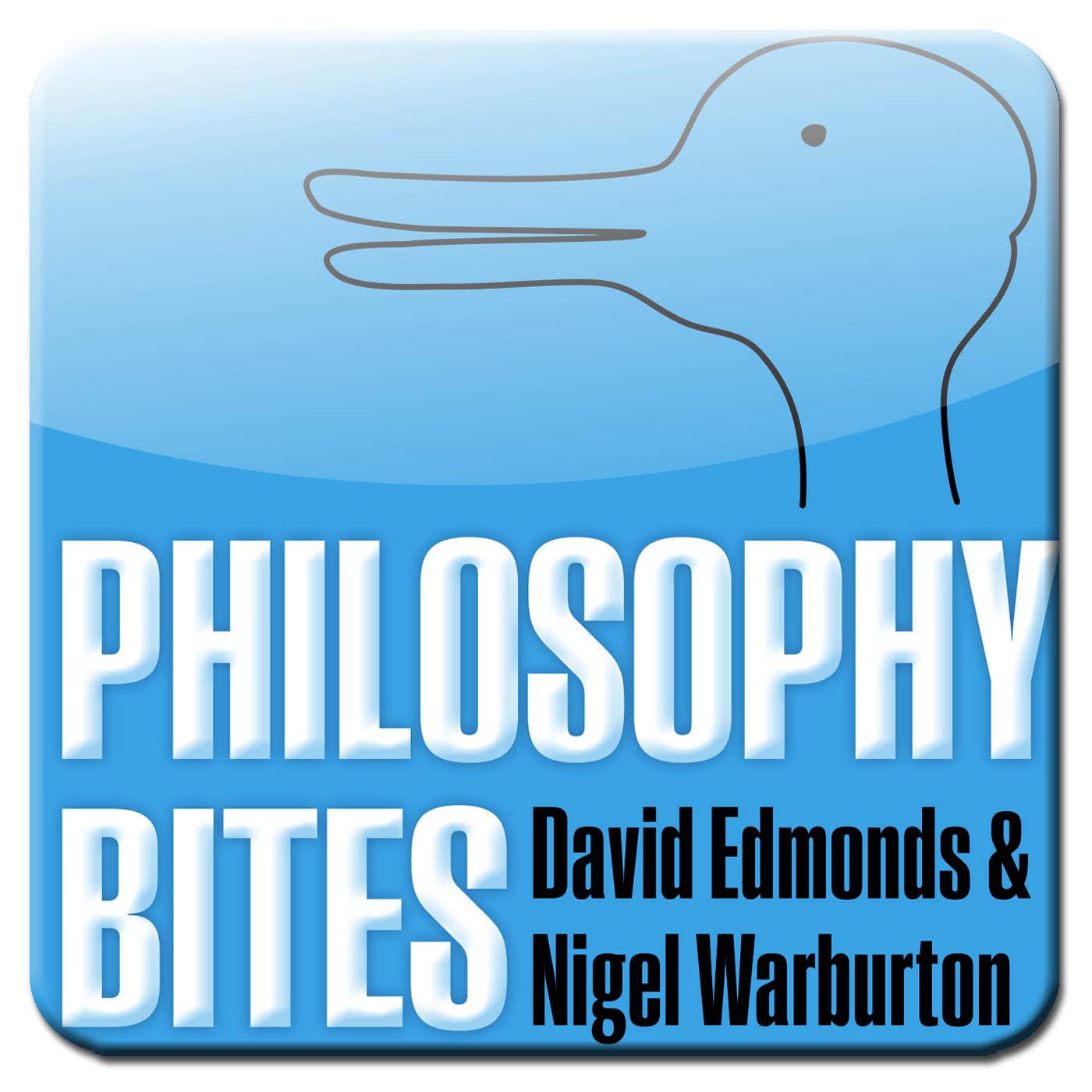
Jonathan Glover on Systems of Belief

HQ's podcast playlist
Deep Dive
Shownotes Transcript
这是哲学点滴,我是大卫·埃德蒙兹。还有我,奈杰尔·沃伯顿。哲学点滴可在 www.philosophybites.com 获取。哲学点滴与哲学研究所合作制作。不同的人对世界有不同的信仰,这很重要。
例如,甲相信基督教,乙相信伊斯兰教。战争因信仰而起,政治因信仰而分裂。对信仰的歧见可能会破坏友谊和婚姻。如果人们有更多共同的信仰,世界将会更加平静,更加和平,当然,也会稍微乏味一些。那么,持有不同信仰的人如何就谁的信仰正确,谁的信仰错误达成共识呢?
乔纳森·格洛弗认为他至少有部分答案。乔纳森·格洛弗,欢迎来到哲学点滴。谢谢。我们将讨论信仰体系。我们能否先说说这个主题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会引起哲学上的关注?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个体通常持有非常不同的信仰。有些人有宗教信仰,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有些人是资本主义者,有些人是自由主义者,有些人是保守主义者。
而且,社会也经常拥有主要的信仰体系,有时这些社会彼此冲突,战争因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而起。如果人们有这些信仰体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这或多或少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一直关注的问题。它关乎思考一种信仰或一套信仰是否比其他信仰更合理或更真实。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哲学家们已经讨论这个问题几千年了,但当战争即将因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爆发时,
哲学家们似乎无话可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所作为。
所以存在这些相互冲突的信仰体系,而信仰体系内的人通常认为他们的信仰体系没有问题。然后是哲学史,它一直都在探讨什么是合理的信仰。但哲学肯定对历史产生过一些影响。嗯,显然哲学家们经常成功。人们说卢梭对法国大革命有影响,或者
密尔对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有影响。人们会这么说,我相信有时这是真的。但这通常是政治哲学或伦理学对公众产生了影响。它不是认识论或知识论,这是哲学的核心部分,它关乎什么是合理的信仰,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真实的。
所以,如果你说的是对的,现在是哲学家们提供一些见解的时候了,这些见解关乎人们如何形成他们的信仰,哪些方法是合理的,哪些方法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呢?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通过谈谈信仰体系通常是如何运作的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认为信仰体系的整体性。如果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开了处方,我会期望这个处方能治好我的任何医疗问题。通常情况下,我很高兴地说,情况确实如此。但如果无效,那就出问题了。我对此充满信心,这是一个预测,所以我的信仰体系中出了问题。
尤其是在科学哲学中,尤其是在卡尔·波普尔的思想影响下,存在一个模型,其中证伪是关键。你有一些假设,你测试它,预测结果是错误的,所以假设被证伪了。这在思考科学以及思考关于世界的理性信仰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简化。
因为当出现问题并且预测被证伪时,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信仰体系的哪一部分。所以当药物不起作用时,我可以说,医生的水平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但这可能不是原因。也许他开了完美的处方。也许药剂师没有正确配制。
或者,也许药剂师完全没问题。也许问题在于我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生化怪胎,所以对大多数人有效的药物对我无效。或者我可以更广泛地追溯。我可以说,也许不仅仅是这位医生出了问题。也许是整个西方医学体系出了问题,我应该改用替代医学。
或者,更根本、更普遍地说,我可能会说,也许是整个西方实证科学体系出了问题,应该放弃它。当我的信仰体系出现问题时,我必须做出一些改变,但我有很多选择,这些选择范围各不相同,关于要放弃什么。
所以你是在说,我们不会孤立地持有信仰,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当我们的一个信仰显然被证伪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直接放弃这个信仰。我们可能会放弃一系列其他的嵌套信仰。那么问题是,我们根据什么来决定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放弃?
你比我表达得更好。我同意,我们确实有这种选择,事实上,关于我们应该放弃哪些信仰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我想要谈谈的是,由于这种灵活性,它们是整体性的系统,信仰存在于系统中,存在于群体中,而不是单独进行测试,这给了人们机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捍卫他们喜欢的任何信仰。
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真实例子是,19 世纪的菲利普·戈斯对化石证据非常感兴趣,化石证据通常被解释为表明进化至少是高度合理的证据。而菲利普·戈斯作为一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信徒,不想改变他对创世纪关于生命起源的描述的信仰。
他说,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上帝决定考验我们的信仰。他种植了看起来像是进化发生的证据,以观察谁是创世纪故事的真正信徒。现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这是荒谬的,但这表明你可以走多远。大概,这些类型的信仰不仅发生在科学背景下,也发生在政治背景下,例如。
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例子的例子是 1939 年英国共产党的情况。许多 1930 年代的英国共产党党员实际上加入了,不一定是由于他们认为卡尔·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相信一切的共有制,或者其他任何可能的原因,
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是因为,在 19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看起来像是希特勒最严重的反对者。
当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达成时,斯大林向英国共产党下达了命令,这些命令被传达给中央委员会,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他的命令如下:你必须停止反对希特勒,因为希特勒现在是我的盟友。你必须说这是一场双方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且你必须做好准备,如有必要,破坏你自己的国家对抗希特勒的战争努力。
这对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巨大的难题。事实证明,中央委员会的一两个人只是简单地改变了立场。这些是命令,我们只是改变路线。其他人说,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存在的全部理由一直是反纳粹。最终他们都同意了,但辩论的记录显示了发生的挣扎。
你把一件事作为你的固定点,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固定点是苏联永远是对的。因此,你必须调整和适应信仰体系的其他部分,以捍卫这一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与纳粹德国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件能让支持新路线更容易的事情是,如果纳粹德国不是一个严重的侵略性威胁,而英国和法国对战争负有更大的责任。
因此,他们开始宣传这条路线。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事实并非德国的实力,而是它的弱点。德国正在拼命寻求和平。现在,从 1936 年开始,希特勒入侵了莱茵兰,接管了奥地利,胁迫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协定中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交给他,然后他入侵了波兰。
这看起来不像一个拼命寻求和平的人,但这表明为了保持固定点需要扭曲系统中其他信仰的程度。
那么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呢?我们倾向于将事物作为一般整体世界观的一部分来相信,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任何信仰。当面对困难的证据时,我们可以选择调整哪些信仰。而且我们也有这种心理倾向,即坚持某些核心信仰。情况肯定令人绝望。
嗯,也许令人绝望,但我宁愿希望并非如此。一旦你意识到你的内心信仰体系,你可能部分地自己构建了它,但通常很大程度上是从你的家人那里继承的,你生活的整个社会,电视,报纸,教堂,你的老师等等。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这很可能会导致那些更善于思考的人转向哲学。
杰出的美国哲学家艾伦·布坎南在美国南部长大。他被许多权威人士抚养长大,这些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他是一个住在南方的白人,他被教导了一系列关于黑人的谎言。因此,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持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直到他开始质疑这一点
他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寻求证据等等。他开始意识到他的权威人物是值得怀疑的,他必须自己思考。他现在与他成长时持有的信仰完全不同。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许多人在大约 12 到 15 岁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内心信仰体系是多么偶然。人们开始思考……
我在这里持有这个版本的基督教或这个版本的自由主义,或者任何它是什么。如果我住在中国,我会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如果我生活在 400 年前,我会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一旦你开始质疑你是否知道它,你就是在做哲学。你是在问什么是合理的信仰。
所以,当你突然意识到你所相信的东西从根本上可能仅仅是因为你的父母相信以及你周围的人恰好相信,它的偶然性,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嗯,哲学中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传统。笛卡尔显然有这个想法。他谈到需要在他所谓的安全基础上重建他的信仰。这就像重建一座房子。你住在一所房子里,你发现它的地基腐烂了。你需要重建它。你首先要做的是,你必须拥有确定性,将坚实的真理作为你信仰体系的基础。
所以他寻找公理。他是一位数学家,对几何学等等感兴趣。所以他寻找具有欧几里得公理等价物的东西,那些你明显知道是真实的东西,然后你从中推导出其他东西。现在,哲学中存在的问题是,根本不清楚是否存在任何没有人可能怀疑的确定性公理。
因此,他的项目被广泛认为,虽然它有很多优点,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事实上,笛卡尔项目的一个显著之处在于,他从 17 世纪法国人的典型信仰开始。然后他抛弃了很多。他重建了系统,不知何故,这个系统看起来非常像之前 17 世纪法国人的信仰体系。另一种模型……
由奥地利哲学家奥托·奈拉特在 1930 年代提出,即你不能完全从头开始。奈拉特说,看待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合理方法不像重建一座房子。这就像重建一艘船,我们恰好漂浮在海上。
也许整个东西都需要重建,但在任何时候,你都不可避免地必须保持足够的东西漂浮,以便你进行重建。这是一个有趣的意象,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你必须让它漂浮才能生存,而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是我们作为人类存在需要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世界的方式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我们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想法。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哲学家都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哲学来继续重建我们的信仰体系。例如,我们必须接受科学的证据。科学的证据通常被认为支持进化论。例如,当哲学家问,我们能否相信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官如何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正确信息?
一个感官系统性地误导它关于世界的物种不会存活很长时间。它们会被一些拥有更好感官器官的竞争物种吃掉。
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论点,但仍然存在一个深刻的问题,即这是否不是循环论证。你所做的是捍卫感官,感官是我们许多科学知识的基础,方法是诉诸科学理论,该理论说我们有充分理由期望它们运作良好。但你是在用科学来证明感官,用感官来证明科学。有些人会说这是一个循环论证。
思考意识形态信仰,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纪的那种事物,大多数戏剧性的冲突都源于那些似乎具有完全不可修改的信仰的人。他们的核心信仰是不容置疑的。
我没有提供某种魔杖,它只会消除人们的教条主义。很明显,相当多的人是相对难以接触的。我建议人们应该进行对话,对话将包括人们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计划,互相询问,准确地说明你的想法。你是这个意思还是那个意思?
这是什么依据?论证是什么?证据是什么?尝试找出假设。第一步是,愿意参与此活动的人会更好地理解彼此的信仰。他们至少会看到差异是什么。然后,也许会发现,不仅内容存在差异,而且内容差异是由智力策略的差异所捍卫的。
例如,一位创造论者和一位进化论者,很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差异,那就是对于创造论者来说,获得真理的基本原则是查阅圣经,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则是查阅科学调查的证据。至少他们会理解。他们深入了一点。他们发现了这种深刻的认识论差异。
然后你可以开始问,它的防御是什么?你为什么认为你的认识论比其他人的认识论更好?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哲学老师,学生带着他们的信仰走进课堂。如果我不同意他们,他们只是认为我在做我的工作,只是为了惹恼他们。但当他们彼此不同意时,
然后,哇,我非常尊重的人,一位同学,持有与我完全不同的观点。所以你会让他们互相谈谈他们的基础是什么。我发现他们通常不会说服对方,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持有他们的信仰。人们不再那么自信了。
最近我一直在教授全球伦理学课程。我们有一些人持有相当传统的穆斯林观点,也有一些人持有相当传统的基督教观点,还有一些人持有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起初,我开始问那些持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观点的人,他们如何证明这一点,以及他们能给出什么理由来说服那些不持有他们信仰的人为什么应该持有它。
他们经常开始有点支支吾吾。那些相信科学实证主义的人看起来很高兴,并且感觉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但是,然后我转向他们说,现在你们相信科学方法。我们为什么认为过去的证据能很好地证明世界未来的样子?我们究竟为什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是可靠的,并且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准确的?
我很享受看到他们也感到有点不安。所以你是在说哲学可以教会我们谦逊一点。我希望我们实际上可能会在某些事情上取得一些进展,我们可能会通过就哪些类型的信仰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达成共识,并据此进行推断,从而朝着关于什么是合理的智力策略的共识迈进。
我们可能无法做到。如果我们做不到,至少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得到,就像,不同信仰体系的地图,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并且不太可能互相争斗。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分歧的例子。关于私立教育存在冲突。机会均等说,让一些孩子享有父母财富支付的优势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自由说,阻止父母花钱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是令人愤慨的。在我认识的人中,相当多的人支持一方,相当多的人支持另一方。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难。
就分歧的性质达成一致。总的来说,由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对自由和平等有点同情,所以我们不会为此而开战,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对方的观点。我希望类似的事情也可能被推广,这样即使我们达不成一致,我们也可能会获得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乔纳森·格洛弗,非常感谢你。
谢谢。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哲学点滴书籍。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hilosophybites.com。有关该研究所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hilosophy.sas.ac.uk。